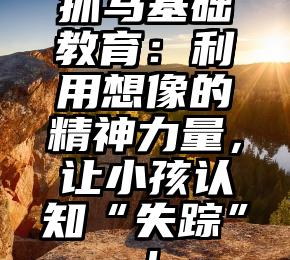是新朋友吗?记得先点中国伦理在线关注我哦~
在这里,与伦理学爱好者在一起~
记忆删除的伦理价值与
数据遗忘权的必要
最近比较热门的新闻,是人人影视字幕组的运营团队由于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而被查处,这个承载着无数人美剧记忆、曾被誉为教育文化交流使者的名字和现象,即将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并不是人人影视字幕组,而是前几年被字幕组翻译的一部英剧《黑镜》,这部在豆瓣上评分颇高的英剧第一季第三集讲了一个关于记忆的科幻故事:人们耳后被植入了记忆丸,作为“个人档案馆”能够记忆每个人每时每刻的所见所闻,想要详细回想某件事、某个人,甚至某个动作细节,只需要操作遥控器,对记忆进行回放即可。没有遗忘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对生活进行复盘,但也带来显而易见的坏处,那就是容易陷入过去不可自拔,男主人翁利基姆就因此而发现了妻子出轨的蛛丝马迹,进而成功地毁掉了自己的婚姻,最终痛苦不堪地割开皮肤,取出记忆丸。

很多人都渴望有个好记性,但完全没有遗忘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上周的“周末闲谈”,我们谈到“记忆删除术与自我认知、自我治理”(可见“周末闲谈”第二篇:记忆删除后,我还是我吗?| 周末闲谈),提到了遗忘是自我的保护机制。大脑为了自我的稳定和存续,会有意无意通过内在或者外在的方式进行记忆的删除、重整,以强化那些正向记忆,而删除那些碎片化或负面的记忆。
然而,这种自我的保护机制,在互联网社会面临失效的危险。我们惊悚地发现,借助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互联网将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包括正面的、负面的,重要的、琐碎的,全都一网打尽、应收尽收。智能算法还将这些记忆进一步清洗、聚类,创造一个与真实自我息息相关、却又脱离控制的“算法自我”,这个“算法自我”,就像个算法幽灵,每天都想着怎么算计我、控制我。对此,我却无能为力。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事情啊!越对记忆深入思考,我们就越会发现,记忆删除和数据遗忘,在智能时代的当下和未来是多么重要。

壹
没有遗忘的互联网带给人的痛苦
互联网没有遗忘,所有的一切全都被记录在案。维克托·迈克-舍恩伯格在其专门论述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代表作《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文宣告,“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人类进入了一个没有遗忘的时代”。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
作者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译者 | 袁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不可否认,记忆对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普及,甚至人的生存、文明的进步,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斯蒂格勒说过,技术即记忆,人类所发展的一整套技术体系,尤其是书写技术、信息技术,都是记忆的外置化、物质化。从远古时代原始人在洞穴墙壁上所写所画,到文明时代日记、书信、报刊等书写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技术对数字化记忆的完全记录,这些由技术构成的外置化记忆,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传播知识进而促进文明的演化。然而,正如《黑镜》的男主角利基姆纠缠于过去没完没了,不能遗忘或者说不能自主遗忘,带给人的痛苦要多于快乐。对于这种痛苦,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那些遭受过人肉搜索暴力的受害者。人肉搜索的基础,就是我们留在互联网上无法被删除、自己又很难控制的数字化记忆。
每天,我们都会在互联网上进行大量的行动,搜索某些关键词,查看浏览某些网页,在微信群或者对话框里与朋友聊天对话,观看某个视频,在知乎提问,在贴吧、豆瓣撰写感言或留言,所有这些行动都会被数字化技术捕捉并留下痕迹。这些数字化记忆,有很多是隐藏的,只被互联网公司所掌握,也有一部分是完全公开的,大家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者网页浏览寻找到;有很多是正面,但也有一些关于个人的负面或者非常希望遗忘的记忆。无论哪些记忆,我们都很难去更改或控制他们,而只能被动地任凭他们影响甚至改变我们。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讲了两个悲伤却又无力的故事:25岁的史黛西·施奈德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她完成了教师资格所需的所有学分、考试和实习训练,但由于个人主页上的一张头戴海盗帽、手举塑料杯喝酒并被命名为“喝醉的海盗”的照片,让她丧失了做教师的机会。有人举报了她,校方也根据这张照片判定她不符合教师的行为举止。史黛西曾打算删除这张照片,可惜网络爬虫早已将其存档,由于“互联网记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记的东西”,她与教师这个职业今生无缘。
另一个故事甚至更冤,60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安德鲁·费尔德玛年轻时曾少不更事服用过致幻剂,也许是为了忏悔,他2001年在一本杂志上记录过这段经历,很不幸的是,杂志数字化了并且把这段经历上传到互联网上,2006年的某一天,费尔德玛就像往常那样,从加拿大到美国去接一个朋友,但这次他没能成功,因为入关时工作人员利用互联网引擎搜索了费尔德玛的名字,查到了他服用致幻剂的经历。尽管是40多年前的事情,但他还是被扣留,并不再允许进入美国境内。

数字化技术让我们个体,还有社会都丧失了记忆删除,也就是遗忘的能力。我们在数字世界,甚至是现实生活之中的每个动作,哪怕是浏览一个网页,搜索一个关键词,甚至在某个页面多停留几秒,都会被互联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无所不包的数字化记忆,就像不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会在我们生活之中通过人肉搜索、告密等形式引爆,给生活带来不便、困扰和痛苦。正如港剧里常说的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由于互联网的不可遗忘特性,我们在网络社会特别需要谨言慎行的德性。否则,要是干了啥坏事糗事,互联网能够记上一辈子,甚至到人死后,还免不了被“掘坟鞭尸”。

贰
遗忘,是自我谅解、社会宽恕
的重要方式
舍恩伯格认为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和全球性覆盖,是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他这只是基于技术层面的考量,数字化记忆的社会动因,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野心和策略,通过将一切数据化,他们能够将一切,包括人的身体和行为都资源化,这样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也就是更自由地进行数字生产、商品推广、信息匹配乃至精神控制。“总体来说,……当前存在一种近乎偏执的趋势:推动万事万物(比如我们的健身规划、排卵周期、睡眠模式,甚至体态标准)朝着数据化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数字化记忆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数字资本主义需要将其全部一网打尽并进行充分的开发和挖掘。(可见“周末闲谈”第一篇:自我剥削:“996”的致命诱惑和华丽伪装 | 周末闲谈)

然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并不需要将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所有细节都详细记忆下来,一来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如此大的容量,二来即使借助记忆外在化的书写技术或数字化技术,也仍然存在着信息空间的限制,三来也是最重要的,出于保护或者维持自我的目的,人类的“自我”特别需要遗忘很多不重要的、琐碎的、负面的记忆。这些琐碎、片面和负面的数字化记忆,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是有碍于“自我认知、自我治理”,因而是内在化的记忆心理机制,或者外在化的记忆技术,迫切需要删除的东西。
人们最想遗忘和删除的,就是那些负面的记忆,包括令人羞耻的过错、令人痛苦的往事,甚至像史黛西那样因为偶尔情绪失控在互联网发表与性格、定位不相符合的言论、图片或者视频。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记忆,这些回忆最初是以痛苦、纠结或者羞愧的形式保留在内心深处,而由于某些制度化的设计,例如忏悔、自我批评、媒体报道,或者其他机缘巧合,却有可能被书写技术或者数字技术外在化、显现化,成为公众阅读、知晓的对象。如何处理这些不堪的记忆,从内在的角度,关系到自我谅解,而从外在的角度,关系到社会宽恕。

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愿提及某个人或某件事,但是现实生活不经意的细节,就可能刺痛回忆的神经,勾引这些痛苦的回忆。当记忆勾连着责任与痛苦,遗忘就成了自我谅解、自我解脱的有效方式,至少通过暂时的遗忘,我们能够获得心灵内在的安宁。从这个角度来说,背负各种痛苦的人们最需要遗忘,最需要记忆删除。
也许,尼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称赞遗忘的,在《论道德的谱系》一文中,他说遗忘并不“只是一种惰力”,而是“一种活跃的抑制能力,一种从最严格意义上讲的主动能力”。遗忘,抑制了记忆,也就抑制了痛苦,让人们获得了一种行动的能力。这样遗忘就与宽恕、行动联系在一起了。在保罗·利科专门论述记忆与遗忘的哲学著作《记忆,历史,遗忘》之中,他非常看重遗忘带给人们宽恕和重新行动的赋能:通过遗忘,人们能够对过错、痛苦进行宽恕,并进而“解除行动者其行动的约束”,让他恢复行动的能力,“做出一些不同于其不法行为和过错的事”。在这里,遗忘和记忆删除,又体现了他基本的社会治理功能,让人得到宽恕,也就得到了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能力。

《记忆,历史,遗忘》
作者 |(法)保罗·利科
译者 | 李彦岑 陈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世界上第一起关于被遗忘权的冈萨雷斯案里

叁
遗忘,也是自我认知、快速行动
的必然要求
即使不只是针对那些负面的、过错的或者痛苦的记忆,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针对我们所有数字化记忆,我们也要重新获得“遗忘”的能力和权利。

图 |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舍恩伯格认为:“遗忘使得我们能够及时地进行行动,知晓往事,但又不受往事的束缚”,“完善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项人类重要的能力——坚定地生活在当下的能力。”《黑镜》中的男主角利基姆,因为深陷过去的失败经历丧失了面对当下和未来的勇气。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识的富内斯》中的年轻人富内斯,由于骑马事故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尽管能够通过阅读积累大量关于经典文学的记忆,但是却不会总结归纳和抽象,无法超越字面的意思去领悟作品的内涵。
如果说上述两则故事都只是文学作品的虚构,那么在现实生活之中,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案例。美国加州一位40多岁的妇女,天生就没有遗忘的能力,因而能记住每天发生的事情的所有细节,包括30年前的某天早餐吃了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个电视节目演了什么,但是如此的博闻强识,并没有给她带来方便和成功,反倒是束缚和挫败,琐碎的记忆限制了她决策的能力,阻碍了她与正常人的交往联系。“如果回忆太清晰,即便这种回忆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决策,可能也会使我们困于记忆之中,无法让往事消逝。”

全盘记忆并没有想象之中那么美好。现实的无限可能性与记忆和技术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数字化空间的容量,并没有大到足以容纳所有一切,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遗忘,才能够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无论是内在的大脑,还是外在的存储设备之中腾出更多的精力和空间,来记忆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才能够轻装上阵、更好更快捷的行动。
学习新东西的前提,是“遗忘”那些陈旧过时的东西。尽管人的大脑并不像存储设备那样,按照格式化删除、重新载入那样的程序进行学习,但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认识论说明了我们的大脑会遗忘那些琐碎的、细节的、错误的记忆,以更好地凸显和强化那些重要的、正确的记忆。因此“遗忘并不是令人困扰的缺陷,而是一种足以救命的优势。当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候,我们便重新获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动的自由。”

然而,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的数字化记忆,却很有可能干扰我们的自我认知和道德行动。第一,互联网上保留的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会不经意地再次进入道德生活,并对我们进行提醒。如果是负面的回忆,那就可能再次勾起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无法自我谅解;但即使是中性的信息,也有可能带来不愉快的感受或体验。例如前段时间,由于工作需要,我上某个APP查询了某个知名企业的公司信息,由于好奇,顺带也浏览了这家企业的几个股东。本来就是无心之举,却没想到被APP背后的算法给牢牢记下,隔不了多久,就向我发送一条短信,告知这几个股东包括那家知名企业又有什么法律纠纷、经营风险等等,不断地以负面方式提醒、影响我,让我分心或者不爽。
第二,数字化记忆会影响并改变我们的信任能力和信任结构。信任既是一种人格能力,也是一种制度化或者技术化的安排。由于数字化技术能够更加保真、更加如实地记录我们的各种回忆,因此当我们内心的记忆不太清晰时,我们可能会更加信任技术化、外在化的互联网记忆,而不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记忆。我们更加倾向于借助数字化记忆存储的信息,来代替我们自己的记忆进行判断、决策和行动。但是互联网上的记忆只是表面看上去客观、真实,他们可能存在被纂改、被操控的风险,也有可能只是数字化技术记录的只言片语。片面地只相信技术,而不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转向。

肆
“遗忘”,还关涉对自我的自主自由塑造
这两天看“孙立平的社会观察”,有篇文章引用了杨鹏与子云针对川普推特和脸书账号被封的讨论《屠杀D-Trump与人类美丽新社会》中的一个观点:在真实社会之外,一个线上的数字社会正在形成。每个生理人都有个相对应的数字人,随着我们的时间越来越消耗在互联网上,生理人越来越向数字人转化,生理人很有可能被数字人所取代,人类真的就要进入数字化生存的美丽新社会。

但是数字化的新社会并不美好,数字人也不是生理人在数字社会的友好孪生。尽管创造数字人所依据的原料,全都来源于真实个体在互联网上浏览、点击、留言形成的数字化记忆,但真实个体不仅丝毫不能自主左右或控制这些记忆,反而要受到这些数字化记忆所形成的“算法自我”的影响和反向控制。疫情期间的有一天,我百无聊赖地打开“西瓜视频”,本来只想搜索一部以前看过的电影,却一不小心点击了旁边的赶海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太魔幻,我居然被这种无心举动束缚整整一天,上瘾似的不停地刷西瓜视频根据这个记录向我推送的各种赶海短视频,就好像我真的是“赶海爱好者”一样。事实上,对于赶海这件事,我除了好奇,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智能算法将我在西瓜视频客户端上的所有数字化记忆都记录下来,并将其与某个表征我的算法身份——我的ID号或手机号绑定结合,进而建模、归类、生成了一个与真实自我息息相关的“算法自我”。这里有一个错觉,表面看上去,西瓜视频是根据“我”的用户画像向我推荐赶海短视频,但实际上这个“我”只是根据我的数字化记忆建模,并根据所有用户数据分类后生成的“算法自我”。具体而言,“算法自我”只是一系列由概率描述的标签,例如“年龄”、“性别”、“收入”、“种族”、“居住城市”、“兴趣爱好”的概率。这个由统计学构成的“算法自我”,可能与真实自我相差万里。

《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危机》
作者 |(美)切尼·利波尔德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正如哲学家安托瓦内特·罗夫罗伊所言:“算法管理完全忽略了现实中受它影响的个体,并给它的唯一主体配备了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躯体’,即不断演化的‘数据躯体’,或者量化细分表格中本地化状况构成的网络。”《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危机》一文的作者切尼·利波尔德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研究细胞生物学的28岁的女性朋友,经常会在谷歌上搜索各种细胞生物学的前沿信息,因此留下了大量此类搜索记录。然而在一项基于谷歌数据的算法游戏“谷歌判定你是什么样的人”里,这位女性朋友居然被谷歌画像为“45—65岁”的“男性”。因为在谷歌所记录、挖掘、清洗并聚类形成的模型里,搜索细胞生物学与中老年男性建立强大的数据关联,以至于将切尼·利波尔德的女性朋友也归于这一类里面。谷歌对你的性别和年龄等身份的认定,依据的是你所搜索的关键词,以及你所访问的网页。“你在线上,并不是那个自己认定的身份。”
由此引出了“算法自我”的最大风险:不仅不精准、不真实,而且不自主。由于互联网平台对算法和数据的技术垄断,我不仅无法决定和控制,甚至都无从知晓,智能算法是如何根据我的数字化记忆来建构和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算法自我”。“经由算法之眼,我们被观察、评估,然后贴上身份标签,但是,我们仅有的反应只是隐隐约约有所察觉——恰似从隐形窗户透过来的一丝风,我们也许能够感觉到自己被监视,但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失去了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个体对自己的锚定,无法进行同步思考”。
由于记忆关涉到自我的认知、建构和更新,而根据我的数字化记忆塑造、却又不为我所知和所控的“算法自我”又无时无刻不准备影响或者已经开始影响着真实自我,所以智能算法通过对我的数字化记忆的全盘记录和分析,就会置我于一个极大的风险之中:我对自己要成为、以及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居然丧失了自主权和控制权。
这让我想起了一则新闻史的轶闻:民国初年,袁世凯平时最爱看《顺天时报》,这个癖好给袁世凯那个一直做着太子梦的儿子袁克定有了可乘之机,袁克定专门印了一份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顺天时报》,上面连篇累牍报道劝袁世凯早日登基的文章。最后正是这些假消息,使得袁世凯相信自己当皇帝,是民心所向。虽说这有可能是个杜撰的轶闻,在数字时代却更像是个隐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通过对我的数字化记忆的全盘记录,创造了一个“算法幽灵”,无时无刻不想着怎么计算我、算计我,“投我所好”却又别有用心。
图 | 顺天时报部分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个人应当好好照看呵护自己的数字化记忆。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个人应该成为自我数字化记忆的负责任的主导者,在互联网的使用方面尽可能地谨言慎行,舍恩伯格将其称为“数字化节制”,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在互联网上的言行举止有所节制和控制,那么便无需过于担心过多数字化记忆会造成负面后果,“既不必担心失去信息控制权,也不必担心暴露在‘数字圆形监狱’或推理能力损害中”。
从消极的角度来说,由于将我们一切生活经历也就是记忆都数字化的最强大动力,来自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追求,那么为了对抗这种无处不在的搜集和利用,我特别主张将“数据遗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关于自己的重要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该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以此维护每个人在互联网时代按照自己意愿塑造自我、成就自我的自主权。
伍
参考文献
1、约翰·切尼—利波尔德,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危机,张昌宏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
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3、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4、李凌、陈昌凤,信息个人化转向: 算法传播的范式革命和价值风险,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5、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学海,2015年第4期
欢迎关注中国伦理在线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 | 张超
中国伦理在线编辑部
你“在看”我吗?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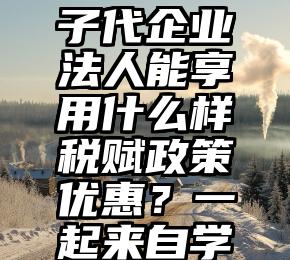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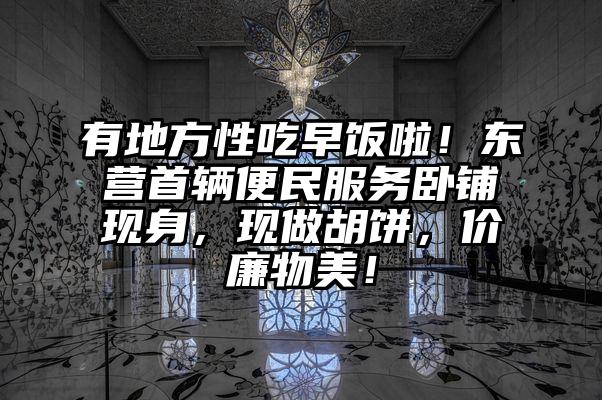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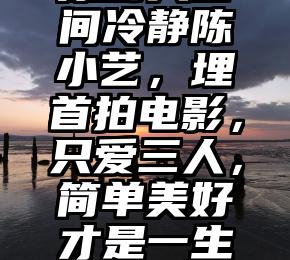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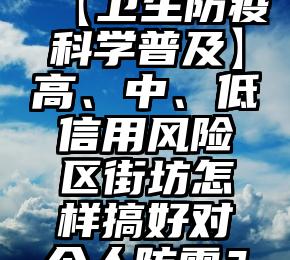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