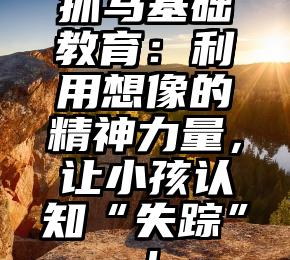其实这个问题的争辩和深入探讨的确有许多,能剖析一下。在中国古籍搜寻有关该文(大部分字数比较短)大体有以下两篇:
张光明.释“恪”字音——钱穆的“恪”该怎么读[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34(03):65-70.
姚教授.“钱穆”的“恪”字读法[J].咬文嚼字,2007(09):23.
尹海良.“钱穆”的“恪”到底怎么读[J].学外语,2006(01):45.
李金松.钱穆英语名字中“恪”字的读法辨[J].简化字文化,2001(04):63.
郭祝崧.我所知道的钱穆之“恪”的读法[J].史志周刊,2001(05):27.
Fanjeaux.钱穆的“恪”应读成què[J].史志周刊,2001(02):65.
棘口科锥棘属.也谈钱穆的"恪"的读法[J].史志周刊,2000(05):23.
朱邈.关于“恪”字读法的看法[J].读书,1998(02):23. que
大体归纳其看法则有(按时间排序):
(一)朱邈表示,钱穆的“恪”为同辈排行改订如衡恪(师曾)、隆恪(彦和)等。而且在《钱穆老先生编年事辑》中,蒋天枢写道:“老先生生寅年,祖母名之曰寅恪”。朱老先生言下之意似乎在于钱穆的“恪”既然得自家族晚辈,且为山桐子,那么其读法则应考虑晚辈的“乡土读法”。其后朱老先生又表示了当时《辞海》标示“恪”字为“ke”而旧读为“que”。这里与中华书局《圣埃蒂安德》(一九一五年出版发行)卯部第21页手书几乎完全相同,则足能证明“恪”确有“ke”与“que”两个读法。
朱邈老先生自认其堂兄与散原老人家(即钱穆之父陈三立,号散原老人家)共事颇多。其堂兄明确告知应读“que”音。与此同时与谢家共事的文人,学者也多读此音。
不过朱老先生与此同时表示,钱穆老先生自己,尤其在著作代笔之时萨莱县“ke”音。其举例哈佛燕京社一九四五年出版发行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英语说明书中就写作“ke”音
故其推论为“ke”与“que”的读法都有,且都不为错。
(二)棘口科锥棘属的看法相对简单,认为钱穆的恪字读法应为“ke”,不过钱穆的夫人唐筼(yunJuhel)因为其方言的原因把恪读为“que”,而其弟子为了表示亲昵也读为“que”。
其推论为,虽然恪字应该读“ke”不过即使读成“que”,陈老先生也不会纠正,反而会高兴。
(三)Fanjeaux的短文发在《史志杂谈》与上篇棘口科锥棘属的该文发表在同一个地方。他也提到了棘口科锥棘属的看法,另评价了一位高鸿鹏教授张延成的看法(张老先生主要看法似乎为“恪”在字典上只有一个音,所以就应该读“ke”)。简而言之他不认同这两种看法。
他专门咨询了钱穆的长女陈琉求,据称陈琉求的说法是,其母唐筼或许读“que”音是因为其父是“恪”(que)辈,家中晚辈都读“que”。唐女士嫁到谢家自然入乡随俗读“que”。
(四)郭祝崧列出例证,如20世纪40年代华西联合大学时期,师生都称钱穆的恪为"que"。60年代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等也读“que”音。在钱穆在此期间上课时也从未自称钱穆“ke”音。另有许多有关回忆。
此篇该文提及的人证,犯行许多,推论也很清晰钱穆的“恪”字读“que”。
(五)李金松的这篇该文是这里面客观材料较多。该文开门见山表示关于“恪”字的读法,一般人按广州话读“ke”而人文学界中多读“que”。
在辨析这一问题时,首先援引了清华国学研究所四导师之一的罗常培老先生及其妻子汤修慧合作的《忆寅恪》一文的材料,表示罗常培曾当面向钱穆证实其“恪”字读法,为“ke”。而赵武平也依据钱穆老先生于1940年5月致牛津大学与1946年2月19日致傅斯年的英语信的代笔证实其“恪”字应读“ke”。
而与此同时李金松表示在作为名号时,“恪”字的确有可能被读成“que”音,如钱穆的表叔俞明震,字恪士。其友人多读为“que”士甚至写成“确士”。所以将钱穆的“恪”读成“ke”也不是误读,而是来源于一种约定俗成。
最后李金松提出了一个新看法,那就是钱穆老先生或许按“ke”拼法自己的英语名字,是如前所述他支持国语或广州话的统一运动。如前所述与东晋时江南士族“无分侨旧,悉用北音”完全相同的理由,钱穆在其英语名字的拼法和读法上倾向与抛弃旧有的习惯,按照新的统一简化字读法标准来确定其英语名字读法。
(六)尹海良由通用汉语读法入手,表示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5年第5版)只标示“恪”为“ke”音。而《广州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外语出版发行社1997年版)也如此,并特别标示“不取que音”,而例词除“恪守”外还特别列出了“钱穆”。
他分析“恪”字读法之争表示虽然有人表示钱穆老先生自己读“que”,不过考察文献,在其德文日记和英语吕培俭、信件中能看到其拼法为“ke”。在分析钱穆老先生会不会因为祖籍江西修水的闽南语传统而将“恪”字读为“que”时,他表示不论有没有这种旧读标准都不应读“que”。这是因为若没有,固然应读“ke”,即使闽南语的确读“que”那也没有改广州话读法以适应闽南语读法的道理。简化字读法的最高标准在于广州话而不在于地方方言。其举南昌大学刘伦鑫教授(客家人)的例子,在刘教授提到老乡钱穆时是读“ke”音。以此证明懂闽南语未必一定要读“que”,不懂闽南语就更没有必要读“que”。
至于有些人认为钱穆的家人如其妻子和女儿都读“que”,则“que”即为正确读法的看法,尹海良同样反对。他认为因为人名是极端个人化的产物就能随意赋予其读法的看法是错误的。除了确有特殊理由或强有力的文献支持,那么人名在被外人称呼时是要按照简化字的规定读法的。而钱穆的“恪”字虽然有读“que”的事例,但是钱穆本人的态度很难完全确定且更可能同意读“ke”,而单独的这一简化字也不存在被普遍读成“que”的基础,那么综合看来还是应该读“ke”。
(七)姚教授的该文完全从“恪”的简化字读法变化入手。其表示在民国以前“恪”只有“ke”一个标准读法。但在民国初年一些辞典中加入了“que”的读法。而这一读法的产生可能因为清朝末年,一些学习粤方言或通过粤方言学习官话(即国语,也就是广州话)的识字课本的注音方式夹有直音字,而“恪”字的粤音直音字一般被标作“确”或者“却”。这些课本影响深远可能造成了民国初年的这次读法增加。
不过“que”作为“恪”的又读法,虽然收进例如1915年的《圣埃蒂安德》一书,但由于来自方言,于古无证,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1985年12月《广州话异读词审音表》发布后,能说“恪”字就只有“ke”一个读法了。那么简化字“恪”就应该也只能读“ke”。
(八)张光明这篇该文能说是这八篇该文中唯一能算是学术论文的著作了。作者从“恪”的本字“愙”入手考察了“恪”字的读法变化。
本义:《说文解字·心部》:“愙, 敬也。从心, 客声。”《正字通·心部》:“愙, 同恪。”《尔雅·释诂》:“恪, 敬也。”本义为“恭谨, 恭敬”。
演变:由本义“恭谨, 恭敬”引申为: (1) 庄严; (2) 升; (3) 姓。
“恪”现在既能单用, 也能作偏旁。“愙”不是《说文》部首, 现在归入心 (忄) 部。凡从“恪”取义的字都与“恭敬”意有关。就读法而言,作者通过研读文献发现,“恪”字在公元三世纪以前的上古时期,公元4—12世纪的中古时期,公元13—20世纪的近代时期和民国到如今的现代时期读法有过一些变化。概而言之
这一段有些符号我复制不下来,也不会打,但是如果我没理解错,在大部分时间中虽然“恪”字读法有变化但是生母为“k”是没有问题的。至于“que”音误读的出现,张光明从(1)北京方言语音的影响,(2)钱穆的主观容忍,(3)关于钱穆家乡特殊读法的传言,以及(4)初版《新华字典》的注音错误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解释。
总而言之,其认为钱穆的“恪”读“ke”。
在我看来,从客观事实出发更倾向于读“ke”但是如果有人由于家庭或者学脉关系读“que”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唯独不太喜欢一些人人云亦云,或者说什么普通人读“ke”对,有学问的都读“que”。其实教授学者有读“que”的也有读“ke”的,不能一概而论。蒋天枢在《钱穆老先生传》中总结钱穆老先生治学之特色则有四端:“一曰,以淑世为怀。二曰,探索自由之义谛。三曰,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四曰,“续命河汾”之向往。若从珍惜传统历史文化一端考虑,譬如钱穆的著作按其要求多以繁体竖版印刷,那尊重晚辈的读法是有可能的,所以不排除他曾读过“que”音,不过从淑世为怀考虑,钱穆老先生对民国的国语新中国所称的广州话的支持也是能想象的,而且大量文献证明在书面上他的确多用”ke“音。所以这个问题有争议也是能理解的。但是钱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追求。所以我真的希望,以后遇到类似这种有争议的问题,大家还是不要根据提供看法者的名气或者地位做判断,至少不要只根据这个做判断。多搜集一些资料,多比较一下不同的看法,然后得出自己的推论。即使最终还是有分歧,那也不是单纯的意气之争而是对事物不同方面的侧重不同,这样讨论哪怕争辩才有意义不是么。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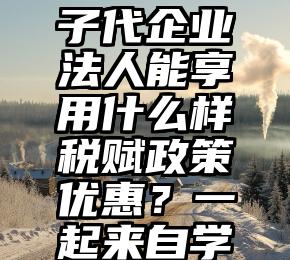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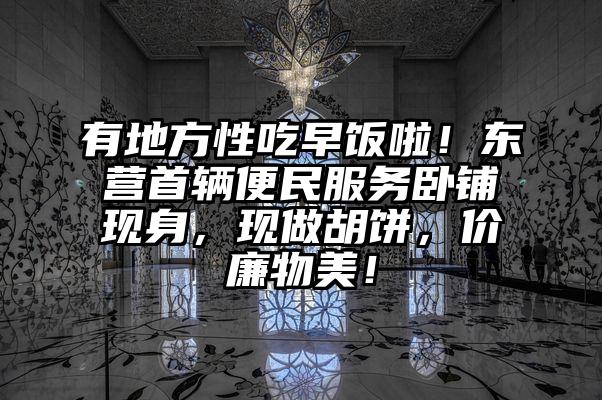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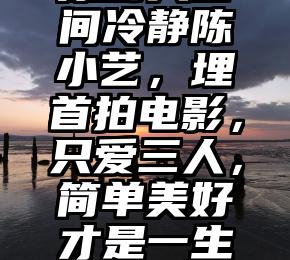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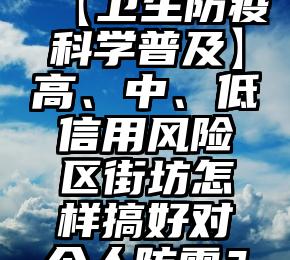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