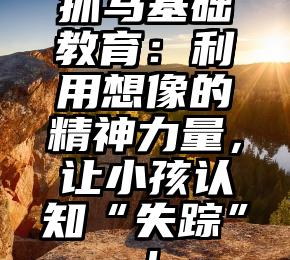作家王朔有篇名为《有个老头九十多》的短篇故事,讲了一个德高望重、为一方俗人所称颂的老头的故事。老头退休后没几年,老伴死了,儿女们便动员他再找一个后老伴,附近的大妈们也有主动上门送关怀的。没承想,一转头,老头竟吞了一把安眠药,自寻短见。
老头的儿子不理解,跟老头急:“您这是为什么呀?”老头不好意思:“太给大伙儿添麻烦了。”老头的儿子叫嚷:“您甭不知足!这么多人待见您。我到您这岁数,还不定趴哪条阴沟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隔了几个月,老头跟旁人说:“多烦呐!我这一辈子就想一个人待会儿,谁也不让。”
王朔离开大众视野久矣。2007年前后,他曾出版几本书——《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随后,除了给《非诚勿扰2》担任编剧,短暂探出头,瞧瞧外面,他再没出来过。
编剧史航评价:“王朔就是那种很想一个人待着的人,待到心里没动静,再等会儿,觉得外面也没动静了,才忍不住探出头,看看外面,结果,又觉得还是应该一个人待着。”
多年前,媒体人王小峰曾在文章中写道:“王朔创造了一个时代,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引领了一个时代,在一个错误的环境离开了这个时代。他不回来,看上去有点尴尬,他回来,也许会有新的尴尬。”
今年,王朔推出新作《起初·纪年》,新书一出,果然生出许多热闹,一众读者吵翻了天。这本厚达706页、煌煌54万字的书,有人爱到不行,甘当“自来水”,逢人便推荐;有人匆匆扫了一眼,就开始义愤填膺、横眉立目地质问道:这写的是历史?

王朔的新作《起初·纪年》。
作家止庵用“求马唐肆”一词来形容后者,并引用鲁迅评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时说过的一段话——“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止庵说:“任何阅读与批评,我们都要得其门而入,明白作者想给什么。就跟旅游一样,你非去海滨城市,吵嚷着怎么看不到山,是不是有点胡闹?”
史航则说:“最早读王朔作品,我正高二,刚上文科班。35年之后,他依然有作品,我们依然在争鸣,多好。”一开始,史航仍把新书当王朔原来的作品来读,但读着读着,发现不对劲,“就像你在自以为的平原上走着,突然一低头,一抹脸,哎哟,流出两行鼻血。好好地,怎么会高原反应啊?再一看,哦,跟以往不一样了,这次是在高原行进”。
《起初·纪年》里面,一帮历史人物甩着京片子,聚在军事会议室里,对着沙盘,拿个小棍,策划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完作战会议,这群人就开始惦记:饭来了吗?咱们待会吃啥?到了晚上也不回家,累了就直接打地铺,一群人和衣而卧。传达室的风大爷更是身担多职,不仅要负责通风报信,还得负责熬粥。
看上去,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聊得特开心,闲了还会互相挤兑。可一转眼的功夫,那些曾经共事的人,一个个都不见了,甚至有的连族都被灭了。
王朔没准备将幽默进行到底。他用了一句“起初,我六年”,轻手轻脚就把读者放进宏大的历史。史航说:“历史残酷就残酷在这里,一群人拿个小棍,拨弄着沙盘,就决定了十几年的烽火遍地、亲人离散,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打着地铺开作战会议的那群人,一觉醒来,才惊觉,这睡的哪里是地板,分明是睡在大雪地上了,就像《红楼梦》里曹雪芹写的那样——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史航看来,王朔在这本书里想讲的无非两件事:这场大雪是怎么下起来的?这个局是怎么散的?起初,汉武帝刘彻像诺亚方舟上的诺亚一般,想带着大家一起走,但这船有裂缝,咕咚咚往里灌着水,哗啦啦往下掉着人。到最后,诺亚方舟成了独木舟,只剩刘彻一人。
史航说:“一群历史人物坐在那儿烤肉、聊天,在大雪天里冻得嘶哈嘶哈,没一个人招呼读者,读者也不用他们招呼。我们知道一切都将付之东流、重归齑粉,可又觉得也是理所当然。”
王朔用极慢的速度,在书中一笔一画写了“孤”与“独”二字。读罢此书,不免生出一种感慨——所谓西汉王朝,不过昨夜一场饭局。
以下是新周刊与止庵x史航的访谈: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
王朔在《起初·纪年》的自序中写道:“当我起大妄想准备上探、觊觎一下我国文明源头,就把自个搁这儿了。这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啦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恍范儿苍孙已然耳顺。”
几年前,王朔告诉媒体,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拒绝透露更多——“我有点儿迷信,没有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人说,就像做饭一样。”王朔像做饭怕揭锅盖一样捂着,可一谈论起此事,眉眼间总是透着得意。
最近,史航见到王朔,发觉他身上带着一种通体的愉快,“他肯定是痛快了”。但很多人看完书,觉得不痛快。哪有这么写历史的?怎么汉武帝及周围一众大臣全都是一口京片子?为什么书里的人称时而是“我”,时而是“上”?
止庵说:“因为故宫的存在,我们大概推断出明清皇帝生活起居的模样。很多以明清宫廷戏为模板的历史小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创作而来。但人们觉得如果凭借这些,就可以准确揣度时间更早的历史题材小说的环境乃至人物关系,无疑是错误的。
“我们读《左传》,能感觉出当时王住的宫殿与街上老百姓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汉代的皇帝也不能比照明清的来写。历史小说其实都是虚构想象的,只不过有些人会试图建构出一种常规理解中历史的模样。
“在《左传》和《史记》中,都曾出现儿童在街上唱歌谣被皇帝听到的记载,如果拿现在的紫禁城去想象过去汉代宫殿的话,皇帝怎么可能听见街上儿童的歌谣呢?
“曾有很多作家从历史中取材,写现代人的故事,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但王朔的创作手法不同,他是捋着汉武帝登基六年直到汉武帝离世,纵横几十年的时间线,书里有很重的史实成分,很多情节都依赖于历史记载。”
 学者、作家止庵。| 图源受访者
学者、作家止庵。| 图源受访者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读后,给止庵发过一段文字,写道:“历史处理材料,小说处理记忆;材料需要准确,小说需要共鸣;历史注重记录,小说关注生命体验。所以,要是按那一套标准要求小说,就没法聊了。写历史大事件,拎几个高光时刻,是相对容易的。而我看王朔这小说,就偏偏喜欢他填补漫长冗余历史非事件性时间的能力。”
历史上,史官们在史书上记载的,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与事件,但中间仍留有很大空隙。“王朔是用他的想象力,把一个个空隙点连起来,连成一条线,把这些空隙给填满了。这条线不是直线,而是绕了很多线头,是一点点被充实起来的。”止庵说。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写道:“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一书中,后羿管嫦娥叫太太,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甚至出现“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等文字。王小波写的《红拂夜奔》,隋末唐初大将军李靖一门心思都在证明数学定理。人们随手就能拦下大隋朝的taxi,但司机并不开车,而是赤身裸体,只穿一条兜裆布,手里拿着一条帆布大口袋,问好了去处,就张开口袋把人盛进去。
对于书中天马行空的描写,王小波解释:“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止庵说:“有些人觉得奇怪、看不惯的地方,可能正是作家们最用心的地方,人家的兴趣点和意图创新的地方,结果到了你眼里,成缺点了。我看了一篇批评王朔小说的文章,里面列出好多地方,质问:你为什么不这么写?可人家本来就不是迎合你的兴趣在写作啊。”
王朔是拿口语(即所谓的新北京话)写作的作者,写完检查文字,也要拿口语来回溜,没磕啵儿才觉得通顺。因此,他每年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冬天一冷,嗓子不舒服,写作速度便会慢下来。去年冬天,编辑希望王朔能写个序,王朔回:“最近烟抽得多,嗓子不好,写不了。等开春吧,开春我嗓子好了,就能写了。”
王朔新书里的人物,甩着京片子,几乎个个都是话痨。王朔自己曾形容:“北京话是一种天生掺水、强调口腔快感的语言风格,见面就聊,聊起来没完,中间一个磕啵儿都不打。”除了北京话,王朔还在小说里夹杂了吴语、粤语以及貌似长安人应说的陕西话,更有外语、网络梗、仿写先秦古歌,等等。这些语言的运用,令不少人费解。
在止庵看来,这涉及语言真实性的问题。止庵说:“古代人应该怎么说话呢?咱们既没有影像,也没有录音,可以考证的只有一些文字记载,但《水浒传》是明朝人写的宋朝事儿,用的是明朝话,《西游记》是明朝人写的唐朝事儿,用的也是明朝话。什么才是准确?
“古代人不说文言文,那只是当时的一种书面语;那半文半白呢,在戏曲中造出来的语言;有人说,应该讲普通话,可普通话是北京话之后出现的,时间上更晚;说陕西话或河南话呢,现在的陕西人、河南人祖上可能根本不在陕西或河南,咱们能想象杜甫用河南话写诗吗?
“没有一种语言是对的,换句话说,你让他们说什么都行。贾行家曾说过一句话——作家得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书写,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用他最拿手的语言写作。王朔最拿手的语言就是北京话。”
王朔将高高在上的汉武大帝,拽到普通人的层面,在帝王生活里注入非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史航形容这本书“胡天胡地不失为人间,亦古亦今不外乎柔情”,称其“对事写荒谬,对人写柔情,最后荒谬和柔情拧成一股麻花”。
王朔的心软,在这本书中亦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从历史的褶皱里打捞出很多未曾被呈现的悲伤、很多缝隙间的历史,人物间微妙的心理,都被他仔细推敲过、咂摸过。
王朔写晚年的汉武帝,在太子死后陷入巨大的悲伤,日日思念——“一夜夜入梦,刚出生,小脚丫;第一次迎风跑,头发飘飘;依偎母亲腿间小手紧擦母亲手,羞怯一掉脸;在笑、在哭、在痛哭,一遍遍演给你看,都是活生生样子。午间小憩也来,好像唯恐生怕你忘记他活过。”
他写汉武帝在临死前,醒在往事中:“往事如花车载哭载笑一趟趟开来,好像一生漫长,其实也不过几件事,要紧的几个人。哭的都是你在乎、最心疼,也曾对不起的人。笑的是欢乐时光同在的人。还有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是你忽略的人。结交相识的人太多,结果是对谁都不好。还有更多黯淡如鬼魅的人,是你殃及、祸及,或因你失去生命的人。”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那本《第二十二条军规》,曾对王朔产生过决定性影响,这本书让他学会了对幽默感的处置和重视。王朔对止庵说,写《起初·纪年》的时候,他还受到了约瑟夫·海勒《上帝知道》的影响。
和很多作家一样,约瑟夫·海勒再没有一部小说,能超越第一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约瑟夫·海勒已经江郎才尽,而是他选择不再迎合大众。
《上帝知道》这本书取材于《圣经》中大卫王的故事。晚年的大卫全身枯槁,奄奄一息,躺在病榻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不过,约瑟夫·海勒没有让这个故事变得沉重,而是一如既往地黑色幽默,用现代的语气吐槽,但读罢,却能感受到无尽的孤独,一如约瑟夫·海勒发出的那句天问:“人独自怎能得暖?”
王朔曾在序中说,自己写到后面写乱了,“乃至最后写丢了第一人称,通篇以第三人称尬然终了”。但止庵认为,“王朔的话不能全信,他这人一直都特别喜欢攻击自己”。
“他用第一人称的时候,一定是我之所见、我之所想、我之所问。等到视野转换到无法叙述时,或情感上的微妙处,他就没法离得太近,这就需要将人称转换成第三人称。他是在用一种‘隔’的办法来写,离得太远或太近都不适合第一人称,都需要隔一下。写到最后,随着汉武帝老去,他对这个世界的兴趣越来越小了,索性全都变成‘上’了。”止庵说。

王朔作品《动物凶猛》。
史航形容:“一个本是天生该当棋手的皇帝,却眷恋于每一个棋子,见每个棋子都不好意思。这种不忍心,用‘我’这一人称时能看出来,但需要杀伐果断、狠心割舍弃子时,王朔就会换成‘上’。这很‘王朔’,他就是典型的嘴硬心软,脸皮忽薄忽厚。”
那些老“古德白”
王朔在《一点正经没有》里,曾描绘过一个“古德白”的形象。一个名叫古德白的老头子横冲直闯进屋,进来就气冲冲找男主方言算账,认为他讽刺了自己。
方言说:“我什么时候讽刺您了?我连一分钟之前有您这么一号人都不知道。”古德白则理直气壮地认为,方言在万人大会上说过的那句“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玩文学”意在影射自己——“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除了我没别人,你没说我说谁呢?”
王朔新书出版后,有人在微信群中发泄愤懑:“王朔才尽且无学,倚京圈之重,以痞子腔与上弓式硬伤糟蹋《资治通鉴》,这是对文化的污损。”
史航说:“看吧,王朔笔下讽刺过的那些老‘古德白’都还在,现在已经进化成了老古德白二世、老古德白三代目。直到现在,这些人仍会被王朔激怒。”
止庵回应所谓“文学京圈”的说法,笑言一旦盖上此章,便“宛如新时代遗老遗少,交游广阔,宾客常满,朋友遍天下,偏财横财大小通吃,人脉不是一般的深广。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北京这地方太大,谁也很难认识谁,即便认识,也不大走动,一年也见不上几面。我跟王朔根本就不熟,到现在只见过两次”。
“我就喜欢看王朔犯贫,他这些话里话外的小贫,揭示着千秋万岁、连绵不绝、煞有介事、巨大的乏。越是跳脚的,越被写在这巨大的乏里面——正如鲁迅《故事新编·补天》里那些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出现在女娲双腿之下的小巧伟丈夫。”史航说。
对于这些争议,自始至终,王朔一直保持着低调。有网友评价称“沉默的王朔和他的话痨朋友们”,史航觉得这种说法很形象,但他觉得应该把“话痨朋友”换成“话痨读者”,“毕竟我们跟王朔真的不熟,都没见过几次面,之所以推荐,单纯是因为喜欢”。
 编剧、策划人史航。| 图源受访者
编剧、策划人史航。| 图源受访者但之前的王朔可不这样,他曾经非常懂得利用大众媒体,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讲见报率”,除非全国媒体封杀此人,否则骂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统计到见报率中去。
史航也说:“其实王朔招儿很多,很懂炒作。在过去,人家相当于是卖时装的,讲的就是吆喝。但现在人家改行了,改卖旧书了。他就支一个小摊,不吭不哼,不打扰任何人,让人家自己挑。”
不少人觉得王朔变味了,借着这本书,感慨属于王朔的时代已然过去。对此,止庵并不认同,他认为作家的写作是有发展变化过程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硬要作家一以贯之地保持一种风格,多少有点刻舟求剑。
止庵说:“不仅作家会变,读者也在变。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读王朔小说的,亲历过王朔最红的时候。但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身边在看书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个年代抢着买的文学期刊,也早已无人问津。”
王朔是读书之人,为写这本书,他下了很多硬功夫。很多人对王朔在书中用“马迁”代指“司马迁”感到不理解,止庵曾问其中缘由,王朔回:“读《管锥编》,见有此写法。”止庵感慨:“他确实有学问,读《管锥编》这事,他人想不到。”
同样出生于北京训总大院,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叶京,曾评价说:“王朔给大众的感觉就是张嘴就来,思维极其敏捷,其实他回家恨不得想十天半个月,为的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也用功,这个用功是他回家做功课去了,不是靠他的聪明在这里跟你胡侃出来的,那是他思考出来的。”
书中“马迁”“方朔”“马相如”尚能找到出处,插科打诨的人名“窦文超”“梁文照”亦能令人会心一笑。可是将司马迁老婆唤作“饼妹”,多少令人费解。史航向王朔询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写140万字,经常会写累,累了就把生活里认识的朋友抓进来,缴获人家名字用一用。”
 王朔作品。
王朔作品。小时候,王朔跟小伙伴在大院里看电影《青松岭》,里面有个爱搞破坏的坏人叫钱广,钱广回家总让老婆烙几张糖饼。有个小伙伴特别爱模仿这段,最后赢得一个外号叫“糖饼”,最后连累得他爸爸都被称为“老糖饼”。
长大之后,王朔津津有味地跟别人讲述这段故事,结果,一转身,发现自己也落了个外号,就叫“饼”,连“糖”字都省了。王朔也不抱怨,认了,他觉得毕竟自己的脸长得太平整,确实像饼。
史航初识王朔女儿王咪时,王咪就曾跟史航说:“饼最近很喜欢做早饭。”
怕人伤心,不怕人不高兴
在王朔早期的小说《浮出海面》中,舞蹈演员于晶跟倒爷石岜约会归来,跟闺密小杨说:“这是一个真人。”后来小杨找机会转述给石岜,石岜心里感动,但嘴上不露,反而装傻问了一句:“太乙真人?”
“明明感动了,却非用‘太乙真人’来打岔,就是典型的王朔。一旦被人识破、被人认可、被人懂得,他就会心生羞涩,开始强行打岔。打岔时龇牙一乐,实际上,他是害羞了。”史航说。
倘若以文如其人的方式去判断王朔,多半会对王朔产生误解。马未都曾评价:“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
王朔喜欢猫,养了好多只。几年前,有人去采访王朔,发觉他越来越像一只猫,“猫睡,他跟着睡;猫起,他跟着起;猫打个哈欠,他也困意袭来”。甚至,他连走路姿势都像猫,端着肩膀,轻手轻脚,悄无声息。
在《起初·纪年》一书中,汉武帝晚年的心事都讲给了猫,“嗫嚅自语人皆不解其意,惟猫知”,王朔更是借着阿娇的嘴,道出那句:“猫是好女孩投胎五次,每一世都必须是好女孩,才托生成猫。”史航说:“王朔总是把女人写得比男人高级,这本书里他是拿女人臊男人,拿猫臊人类。”
除了家里养的猫,王朔在家附近还喂养着三拨流浪猫。这三拨猫,来自三个不同的阵营,见面就掐架,王朔便分成三个食盒,分别放在屋外不同的地方,等着流浪猫来寻食。“搁谁能有这耐心啊?”为此,史航给王朔起了个外号,名曰:真·王大善人。
王朔内心有一片特别纯净的地方。在与作家孙甘露的对谈中,王朔提到自己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一看到《魔女宅急便》,总能想起好多事,想起在青岛当海军的日子”。除了《魔女宅急便》,王朔还喜欢《千与千寻》,因为“动画里没坏人,最坏的汤婆婆,也就是要你给她干活,不是要夺你性命,想着就放心”。
 王朔。| 图源豆瓣
王朔。| 图源豆瓣最近,王朔告诉止庵,他很喜欢桥本爱演的《小森林》,“一个女孩子吭哧吭哧在那儿埋头干活,做饭就用自己种的菜,这片子拍得特别纯净”。
但“痞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了王朔这辈子都摘不掉的标签。王朔自己也懒得摘了,甚至顺势一再强化这种形象。
史航说,王朔的痞,其实是一种真实,他总是试图指出一些问题,就像那个在人群当中,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动物凶猛》里,米兰问马小军:“你觉得这样有劲吗?”马小军嘶吼着回:“有劲!”其实潜台词是没劲,大家的生活都挺没劲的。
王朔经常用他的创作提醒别人,刺痛别人,更因此惹恼了别人。但“痞”字拆开是哪两个字?一个“病”,一个“否”,毛泽东曾在一首词里写过,叫:“人有病,天知否?”大概意思是:有病需要救治,上苍可知道?王朔的痞,是在戳破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
王朔就像《看上去很美》里面的方枪枪一样,为了获得小红花,争取过、努力过,甚至试图理解过规则,尝试着融入集体,但统统失效。后来,他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希望吸引别人注意,结果仍是被孤立、被嘲笑。之后,他索性开始配合表演——你不是说我痞吗?那我就痞给你看。再后来,王朔连这种对抗的兴趣都没有了,直接闭门不见客。
史航一直好奇王朔为啥不爱出来见人。一次,他听王朔跟别人聊起此事,“不爱跟人见面,见面三分情,见面就忍不住对人好,什么都答应”。在跟孙甘露对谈时,王朔也曾透露过:“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怕群众。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到门口我进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惊着了。”
王朔是怕人伤心、不怕人不高兴的那种人。如果真惹得谁难过了,他心里肯定百般过意不去。但如果不触及人的伤心处,他倒是不在乎对方高不高兴,甚至常会做出一些扫兴的举动,露出一副扫兴的神情。不过,这并非他故意为之,而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自然流露。
作家赵赵曾在一档对谈节目中,看到王朔接受采访的模样,喊来自己老公唐大年,指着电视里的王朔:“来,你看看什么叫臊眉耷眼。”这段经历,后来被王朔写进书里。王朔日常就是一副臊眉耷眼的模样,在这本《起初·纪年》里,他就是以臊眉耷眼的姿态来书写的,用史航的话来形容,“臊眉耷眼写春秋”。
王朔是一个禁得起骂的人,他骂自己,甚至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狠。在《我看王朔》这篇文章里,王朔写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王朔,才能证明我们的文学是繁荣的、百花齐放的?”他形容自己的文字是“文学这一母体下的崽儿甩的子儿变出的幺蛾子”,甚至带着起哄的架势,喊出那句:“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在这一点上,嘲讽他的人确实需要反省。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否骂出了新意?史航曾形容那些来不及阅读就急于发表评论的人,是活脱脱的“B超型书评人”。“怀孕做B超,不是男孩就是女孩,这些人扫一眼书,要么合我意,要么不合我意。一不合意,就开始骂人。骂的内容,颠过来倒过去,也就那么几句。”
王朔虽然禁得起骂,但禁不起夸,稍微夸他两句,就开始浑身难受。用王朔自己的话来说——“名实不符,都是债”,他生怕自己担上无用的“债”。史航笑言:“王朔有恐高症,离地半尺就受不了,稍微高点就开始嚷嚷,‘快放我下来’。”
透过王朔过往张牙舞爪的表象,你会发现,他有着很深的自嘲与自省精神。他曾在《昆明周记》中回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在人群后面喊台上的人‘傻帽’喊多了,现在怎么也不习惯往人前站,总觉得还有一个自己远远躲在人后头喊‘傻帽’。”
如越王勾践般,耳畔总会响起“你忘了亡国之耻吗?”,王朔的耳边似乎总在响着:“傻帽!”这里面骂得最响的,恐怕就是他自己。这一点,参照王朔之前给自己起的书名便可略知一二 —— 《千万别把我当人》《谁比谁傻多少》!
 王朔作品。
王朔作品。王朔一度非常高产,叶京曾评价:“大众的消费文化扑面而来的时候,大家打开电视天天看到的都是王朔的名字。”但有一天,王朔走在大街上,突然觉得精神大厦轰然坍塌,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丢失,他的生活没了。打那以后,王朔开始抗拒写作。
2001年,王朔更是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崩溃,他在书中写道:“梁左去世、我哥去世、我爸去世,迎面给了我仨大耳刮子,基本把我抽颓了。”
那段时间,王朔经常躲在家里,思考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觉得周遭的一切都不真实,人们的喧哗、拌嘴都没意思了,他进城走机场高速,时常感觉一片片灰树林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生的尽头。
王朔开始找各种心灵解药,他开始研究佛经、圣经,甚至开始翻中学物理,但这些都给不了他答案。直到一天,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就写作这一个专长了,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剩写作陪着,于是他再度拿起了笔:“写作治糟心,写出来就等于把糟心存电脑了。然后自己就成别人了,可以坐在桌前充满关怀地想,怎么把电脑的糟心解了。”
对王朔而言,现在的写作,纯属为自己过瘾。所以,趁早别用之前那套要求他、评判他了,就像他之前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我说不了那些气盛的话了,开始学一些老谋深算,锐气是不复当年了,谁要还想看我的小说解气,浇心中块垒什么的,肯定要失望。你们自己往上冲吧。”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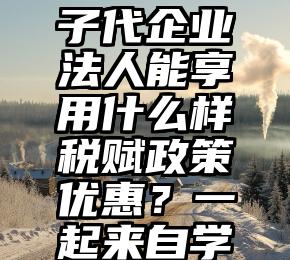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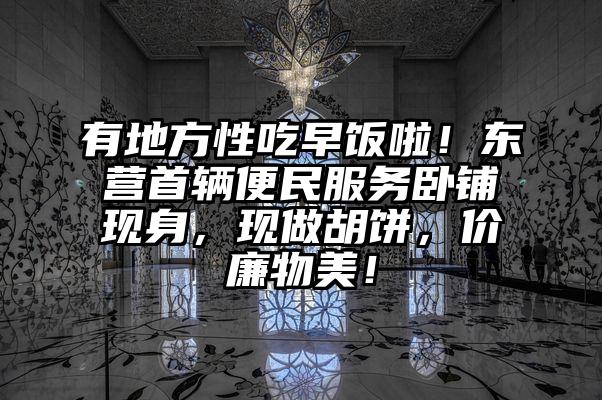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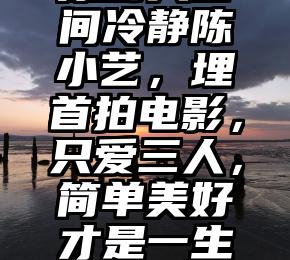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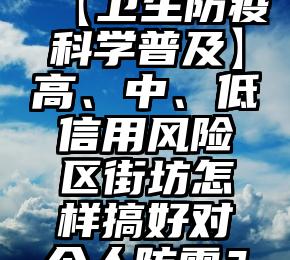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