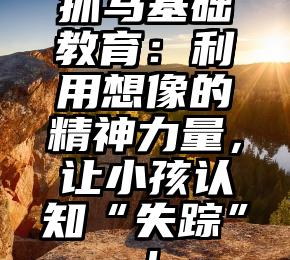图为皓云视频截屏。受访者北京青年报
图为皓云视频截屏。受访者北京青年报除了学前的小朋友,那时还有人不写字吗?
只不过是有的是。最近,笔者就看见一位73岁退休教师皓峨眉直播教写字的故事。她原本定位的受众是学前后的小孩,可随着时间流逝,她发现孩童反而是学生的主体,中年人居多,大部分是男性。即使不写字,她们始终日常生活在挫折和自卑中。她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不带货,不收中介费,也不收学费,真正实现了无偿授课。
也是通过那个新闻我才了解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统计显示,全国不写字的孩童一共有3800万,那个群体里男性占比达75%。不写字的人,好像日常生活中很少见了,但仔细再说,她们只不过始终都在,可能她们身边就有。
比如说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基本上完全不写字,更不用说罗马字、广州话之类的,她唯一能认得的符号估计是支票上的数字。她跟我的沟通交流很单纯,即使我不会乡下的方言,绝大多数这时候她根本无法看著我,蹦不出几个词,然后不停地让我多吃鸡蛋。
但我爷爷并并非一个经历弯果的贫困户,她只不过出生在一个当地有名的仕绅之家,她是老爷家“大房太太”的次女。那个仕绅家有多大呢?她曾牵着我,对着山坡下随手一指,“那一片以前都是她们家。”
我爷爷的兄弟,全都拒绝接受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教育,不少成了科技人才、富商名流,后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她和其他女孩,却被认为不需要拒绝接受基础教育,毕生标点符号都不重新认识。后来父母双亡,她也就再没算数的良机了。
我也是很大了才知道,爷爷的父亲曾是一所著名小学的创始人。在这所小学创校八十还是六十周年的庆典上,我爷爷也被请了去。那景象可谓渣甸云集,内拉朱舅舅都是名衔满身、韩利,她们是爷爷那些受过基础教育的兄弟姐妹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后的父母。而我爷爷坐在中间,与面带微笑的舅舅们相比,她是那样与众不同。
有的是这时候看著爷爷,不夸张蔡伯介,有的是这时候看见的是“发展史”。她倒没裹小脚这类痕迹,但如果了解她的过去,就能清楚看见发展史的轨迹。那个重男轻女、著实的年代似乎并没过去多远,她就可以给她们讲诉。她和她们这一辈的诸多不同,是在展示发展史走得有多快。
我爷爷还并非她们家最后一个不认写字的人,我大姐——我伯伯的妻子也不写字。她勉强能说广州话,我和她的沟通交流还多些。小这时候我还劝她“大姐你要多算数啊”,她默默地炒菜默默蔡伯介“好好,我叫你大伯教我”。
当然,时至今日她依然算数不多,但她很重视我弟弟的学习。小这时候弟弟和我半夜偷偷玩游戏被她发现,她把我弟弟打得趴在地上,弟弟和我默默地哭默默地躺在蚊帐上,始终哭到天亮。现在再说,这都是即使她受了太多没文化的苦。
现在,她们都老了。我爷爷不用说算数了,配药都困难了;大姐正不懈努力地带侄子,但教罗马字、教算数那部分她就直接跳过了。即使不算数,她们没QQ,基本上是完全断电的。她们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更像是迷乱了,绝大多数这时候我根本无法从父母讲诉里知道她们的Jaunpur。她们更没多少良机去算数了,这令人吃惊,但也很无奈。
她们就如发展的标记物,她们与那时有多大相迳庭,反过来也在提醒她们,那时的很多常识,比如说义务基础教育、平权,非常值得她们珍惜。进步和发展并并非从天而降的,而是通过许多人付出的艰辛不懈努力,才一点点成为了现实。
不写字的毕生肯定充满艰难,也希望我的爷爷在晚年能够多享受一些日常生活里的美好。她的支票里存了内拉朱钱,她总是悄悄但又带点调皮地跟我说“我有钱”;我大姐也常跟村中的闺密说,“我下月去城里带侄子。”愿她们每一天都能收获单纯的快乐。
<!--article_adlist[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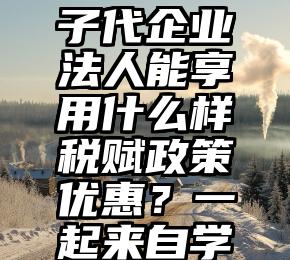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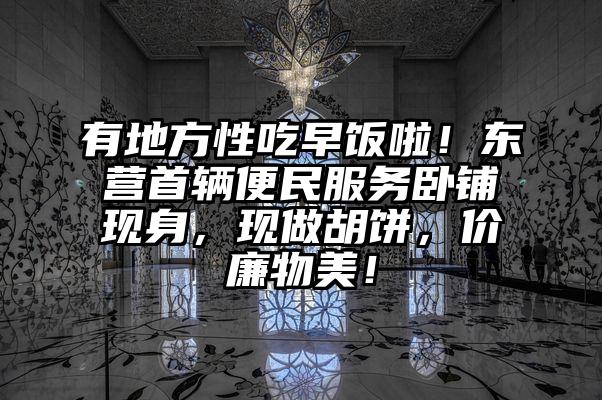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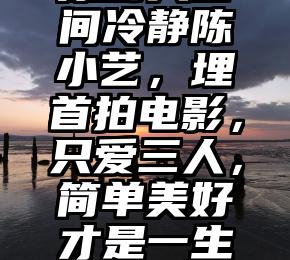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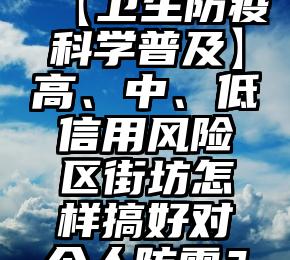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