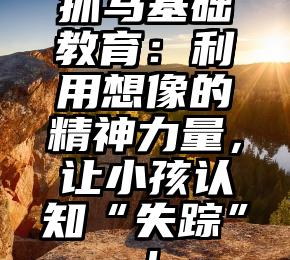恪字到底是不是读
.jpg)
钱穆在副手刘刚帮助下已经已经开始著成(为于Daye)
.jpg)
没教授名衔的钱穆,却被称作莲花池中的总貌、副教授的副教授。
.jpg)
1947年钱穆与费孝通副教授
.jpg)
后半生的钱穆失聪,但他总有一天睁大着双眼,黑髯鼠。
.jpg)
.jpg)
钱穆与父母1951年在深圳
从上世纪20二十世纪已经开始,有关钱穆的巨作故事情节,就始终在莲花池里广为流传着。即使他的英文名字,也被现代人屡次探讨——前年,北大每边都叫他钱穆(què)老先生。不过在许多词典里并没恪(què)这种的读法,没人求教他:为何我们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未予纠偏呢?王老先生笑着反反问:有那个必要性吗?他或许更期望现代人介绍他的学识或其商业价值,他的整座心灵是和学术研究相连接的。他在悼、家恨和对个人的曲折中,为学识牺牲了毕生。
——编辑
中国网
.jpg)
王继如,男,苏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指导老师。出生于1943年,东莞肇庆人。1966年大学毕业于苏州师专(今改交大);后师事文字学我们徐复老先生和文献学我们张舜徽老先生,获文学硕士和历史学教授学位。长期从事文献语言的研究工作。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副教授。主要著作有《训诂问学丛稿》、《敦煌问学丛稿》等。
首先,我以为那个探讨是很有意思的。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应该如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变,应该如何研究;三、语音演变中的特例,应该如何对待;四、从这些问题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恪到底应该读什么音。这关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的问题,也就是颚化问题。那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了。迄今为止,其基本规律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口必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开口大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存在相当普遍,二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那个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法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规律。两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这自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字。按照那个办法,将恪的读法规范为kè是恰当的。
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种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確的简体字,而確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所以確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声),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周汝昌老先生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多数是颚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如客字,周老先生文中说其家中的保姆读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说违背规律。但北京话仍念kè,所以规范的读法是kè。嵌虽然也有许多方言读kàn,但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周老先生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这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的道白也如此念,这种的读法还有很多地方,如苏州、江淮等地。这只能说明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法。而京剧本来就要求分尖团,用这种的读法是正常不过的了。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契丹之契,是四等字。俄语中契丹对音为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说明当时俄国人听到的那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法,这些不同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还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语言材料。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法。这种状况,音韵学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转的。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相近相通之处。周老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如果确实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就是一音之转。而且,可是一等字,这种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那个例子,是成问题的。可,犹恰也。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已经说过。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西厢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说实承张相。不过,张相可要审慎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以训为恰,并没说可可以读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节,是果摄一等字。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角去寻路径呀!用那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是不是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有相当多的证据。不可不谨慎。
据上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为何可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老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做了点猜想。吴老先生说愙字京津读为què。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京津地区也许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què了。《集韵》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是个二等字。据丘驾切折合成今天的读法,就是qià了。吴老先生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恪在现在那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法应该仍为kè,读què则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但是,如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事实。那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同时发生同一变化,出现聚族而居的状态。鉴于这种理论和语言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老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纠偏它的缺陷。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法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化,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变化的。只要那个过程还没完成,就可以观察到不规整的现象,即所有应该变化的字中,有已变的,有未变的。而率先变化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韵位置没使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那个理论来看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汉语的颚化过程,也许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典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了(友人马汉鹏说,他曾在该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变化的不规整状况,吴语中也如是,龟、鬼、跪、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等不颚化。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州大学马贝加副教授说)。
那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没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颚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其音韵位置又不太明确,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却是二等,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原因,就让它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恪的正读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回头再看王老先生对他的英文名字中的恪的读法处理,以为正读是kè,而又不去纠偏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者的眼光呀。(王继如 光明日报)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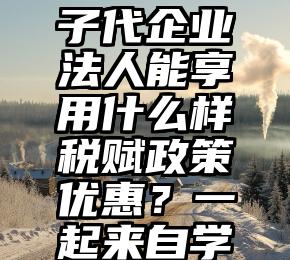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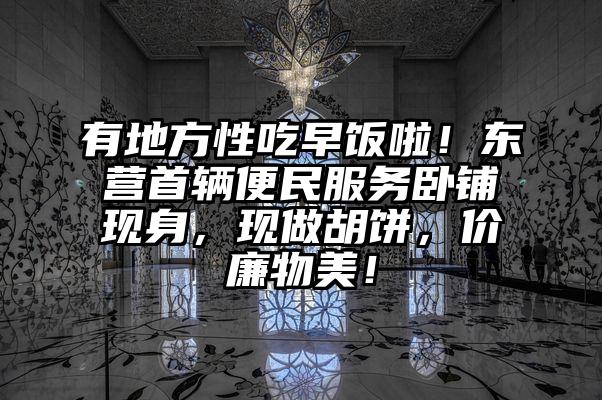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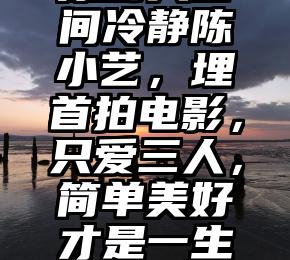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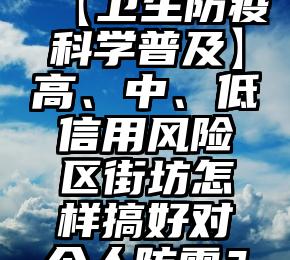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