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樊曦的QQAvold“老象”,三个字研磨地归纳了他的条码:第一,他去年已70岁了;第二,他的首篇鸟类短篇小说写的是大象。从1980年发表首篇经典作品《象群迁徙的这时候》至今,樊曦已经写了40多年鸟类短篇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短篇小说《狼王梦》更是80后90后的童年集体记忆。
象、狮、狼、豺、狐、狗、猪、鳄鱼、骆驼、天鹅、鹰、雕……有人数过,樊曦写过70多种鸟类,但似乎都是海岸线上的鸟类,近日出版的《极地之歌》补上了这个缺,写的是宽吻鳄鱼——这是樊曦第二次“下海”。
樊曦也桑桑很多鸟类:1969年插队落户到傣族的村子,猪牛羊都桑桑,家犬吃什么?马也桑桑,即使那个地方性没车,上山只能靠骑马;桑桑鳄鱼,当地老百姓还送给过他一只“黑猫”,下蛋半大不大这时候,才发现是只黑豹;家里两千多有7目褐,现在有一只猫,还偶尔游荡蟋蟀、蝈蝈、金铃子……

樊曦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过70多种鸟类,为何第二次写极地鸟类?
樊曦:我出生在上海,但上海的城区距离海还有两公里,而且长江入海口是黄色的,没远方的颜色,也没远方的气势,因此对极地并不熟识。
1969年,我到四川傣族插队落户,在那儿日常生活了几十年,因此我过去的经典作品大都写的是我熟识的四川的鸟类。傣族不靠海,自然也就没极地鸟类。唯一写过的水生鸟类是《大鱼之道》中的黑鲩,也是澜沧江的淡水鱼。
那为何要写极地鸟类?即使有冲动,即使我知道极地是心灵的摇篮,大部份心灵起源于极地,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陆生脊椎鸟类的祖先,是由鱼类在4亿年前从远方迈向海岸线进化而来。这种鱼叫做文昌鱼,现在在福建、东莞中心地带的极地里,渔夫还能钓到这种“活化石”。
我被大家戏称为“鸟类短篇小说大王”,但从来没写过极地鸟类,我自认为是一块短板、一类缺憾。加上写了40多年,人们熟识的鸟类种类我都写过了,再写难免有“总而言之”之嫌,很难有新意。想要突破,我觉得有三个方向:其一远古鸟类,其一极地鸟类。前者我写过侏罗纪的“五彩始祖鸟”,后者就是这一次的宽吻鳄鱼。
我去年70岁了,但觉得还能写个七八十年,希望这段时间在文学艺术上有所追求、有所突破,起码不是原地踏步。
中青报·中青网:写极地鸟类有什么困难吗?
樊曦:难的就是我对极地鸟类不熟识,因此这本书写得南蒂阿县,从构思到完稿将近5年时间,当然期间也写了其他经典作品,但这是我大部份经典作品中耗时最长、耗心血最多的经典作品。
其间,我时常去大连、威海、青岛、珠海、深圳、宁波、舟山这些地方性采风,和渔夫闲聊,闲聊是补课、是做功课,因此时间线拉得很长。
中青报·中青网:为何第二次写就选择了鳄鱼?
樊曦:鳄鱼是一类和我们人类文明比较吻合的极地鸟类。我和老渔夫闲聊的这时候,讲到鳄鱼,不光是东莞中心地带时常有鳄鱼游荡的地方性,老一辈人就会给我讲类似的故事情节:原来条件差,小渔船是木头做的,渔夫碰到暴风雨,船就会倾覆,甚至被风浪解体。渔夫落水后,如果附近刚好有鳄鱼游过,不光是宽吻鳄鱼,它们会“出手”救人,用自己的背把渔夫勾出海面,然后送到海滩。
即使是过去没宣传要保护鸟类的年代,碰到鳄鱼在海滩上搁浅,附近的渔夫发现后单厢主动来救援,把鳄鱼重新送回远方;如果不幸鳄鱼死了,渔夫会把它埋葬。在世世代代的渔夫心中,人类文明最忠实的朋友是鳄鱼,其他极地鸟类也许是食物,但从来没听说谁吃鳄鱼。
鳄鱼还很聪明,从脑容量和身体重量的百分比来说,鳄鱼和人类文明很吻合。鳄鱼会唱歌、会科泡;还是跳水运动员,经过简单训练后就能表演很优美的节目……但即使鳄鱼和人类文明如此吻合,人类文明对真实世界的鳄鱼日常生活也不是不光了解,因此我选择写鳄鱼。
中青报·中青网:《鳄鱼之歌》中的三个故事情节,有三个结局都不圆满,甚至有些残暴,充满死亡与背叛,为何这样设定?
樊曦:我认为鸟类世界的本质就是“适者生存”,这是一个残暴的过程。鳄鱼是一类有群体意识的鸟类,是群居鸟类,内部既有团结凝聚力,又有激烈的竞争。我想真实世界再现鳄鱼这一物种的生存状态,肯定会写到其中的艰难、残暴与无奈。
中青报·中青网:曾有人批评你的鸟类短篇小说太残暴了,不适合小孩写作。
樊曦:鸟类短篇小说不是童话故事情节,童话故事情节是香软的、甜美的,即使中间有悲情最后也是大团圆的,这是低年龄段小孩对童话故事情节的需求。我的鸟类短篇小说一般是中低年级的小孩写作,他们应该有限度地接触真实世界的日常生活、真实世界的社会。
文学要忠于日常生活,写鸟类短篇小说怎么能躲避荒野自然法则。野生鸟类世界天天都在上演意外事件,鸟类短篇小说也就免不了写意外事件。当然即使我的读者是青少年,我也会有所节制。
中青报·中青网:那这个“度”在哪里?
樊曦:我表达的主题在于,幸福的东西、心灵的力量,不会随着个体被消灭而烟消云散,它会变成一类精神上的基因,救世承。
《鳄鱼之歌》中的“半脸鳄鱼”即使受到核辐射而容貌毁损,造成意外事件,但它的善良与对幸福的向往,在这个族群中传承下来,它的后代也因此得到了善待;“恶龙鳄鱼”虽然最后死于非命,但它为族群开拓了更好的生存空间,把爱冒险的性格转化为勇于开拓精神,这是符合心灵发展逻辑的。
因此,这个度就在于,有没幸福的东西传承下来。生死的意外事件在不断上演,但心灵总体来说是顽强生存、追求辉煌、一代胜过一代。
中青报·中青网: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鸟类?
樊曦:狗,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一目褐。
2004年,我从部队转业,举家从昆明迁回上海。当时昆明家里有一条养了7年的狗,即使有点胖,我们给它起名“阿福”。我们觉得阿福的年纪大了,换个环境可能有问题;刚在上海买了房子,手头比较紧,而运鸟类无论火车还是飞机都挺贵的;运输还需要各种证明,比较麻烦……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它留在昆明。
于是,我们找了很要好的朋友老丁,他家有比较大的院子,我们每个月给他一些补贴,买点狗粮,请他帮我们照看阿福。老丁满口答应,于是我们就回了上海,隔三岔五打电话去问,老丁总是说阿福很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呢。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突然有一天老丁打来电话,说很抱歉,阿福跑掉了,找不到了。我们当然很着急,请老丁好好找一找。又过了10来天,那天深夜11点,老丁又打来电话,说他刚刚和朋友喝完酒,路过我们家在昆明的房子——当时已经卖掉了,结果看到一目褐在单元门门口蹲着,“我过去一看,就是你们家阿福!我叫它名字想把它带回来,可它一看是我就扭头跑掉了,我没追上”。
接完这一通电话,我儿子哭得稀里哗啦,我和太太也不光后悔,最后决定由我这个时间相对宽裕的人,带上两万块钱,第二天就买机票飞昆明,一定要把阿福带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飞机火车不行,租一个车也要开回上海。
到了昆明,我住在原来住址边上的一个小旅馆,白天睡觉,晚上就去单元楼下守着,希望阿福能再次出现。守了整整7天,阿福一直没出现,我也不能长时间不上班,只能抱着深深的伤感和遗憾回了上海。从此,我们再也没接到过阿福的消息。
阿福一定成了一条流浪狗,我只能祈祷它能找到一个新的好主人收留它,开始新的日常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一想起阿福,总是伤感和愧疚。我写过很多野生鸟类,却没写过城市里的鸟类,于是去年我和几个年轻作者一起写了“流浪狗奥利奥”系列。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写鸟类短篇小说的过程中会有什么困惑吗?
樊曦:就是鸟类短篇小说的写作标准。在西方的鸟类短篇小说中,鸟类大都是幸福的、善良的,人类文明是丑陋的,或者说在鸟类面前是有原罪的,大抵是这样一条脉络。但我认为,鸟类短篇小说所表达的哲理,可以是更多样的、更丰富多彩的,比如鸟类的母爱、挣扎求生的智慧,等等。
西方追求比较精细地表达人类文明观察到的鸟类的真实世界情况,这个我觉得纪录片可以做得更好,比文字震撼多了。在现代化的观察手段面前,鸟类短篇小说的优势不在于谁更真实世界,而在于鸟类的某种行为对人类文明的震撼力。
有人觉得我描写的鸟类世界像人类文明社会,那你怎么知道鸟类世界就不是这样的呢?比如找对象,鸟类要找长得漂亮、身体好、忠诚度高的,很多东西并不是人类文明独有的。我承认笔下的鸟类有人的思维心理,但我可以反过来问,你怎么知道鸟类没这样的思维心理呢?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樊曦:我要写一个关于远古生物的故事情节。远古时代,极地里有很多巨型鸟类,有一类鸟类即使体型小,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于是只能向大陆进军。成功登陆后,它们非常开心,一开始也过得非常幸福。但随着时光流逝,日常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在海岸线上又碰到了恐龙这样的庞然大物,没办法,为了生存,它们又被迫回到远方……
故事情节讲的是心灵的循环,每一次循环似乎是回到原点,其实是进化为更高层次的心灵状态。
责任编辑:郭韶明
<!--article_adlist[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article_adlist-->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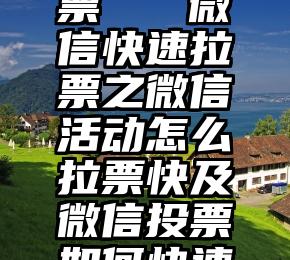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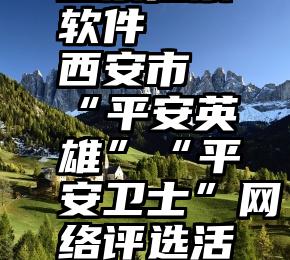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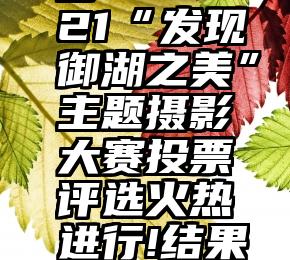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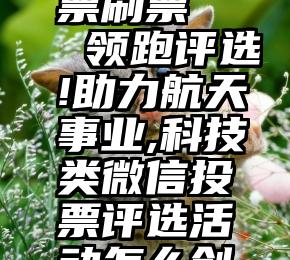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