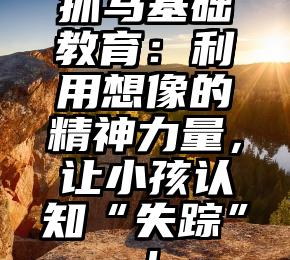我有两个好友。
他们都叫他萼距。
他们俩是是不是重新认识呢?
初三的这时候,他跟顶楼班的打人,我给他猛推两条后卫线腿,最终背他到了疗养院……
好吧,这是编的。
事实上就而已即使两本叫作《恶棍是什么样锻造》的短篇小说,译者六道轮回。
晓得那个书的,都曝露岁数了。
那个书讲的,是两个好小学生正式成为道上小弟的故事情节。
黄大仙区不才,高中的这时候,也考出数次班上第三,勉力算是句好小学生。
而像我此种楚楚可怜,十分眷恋此种好小学生也能正式成为道上小弟的戏码。
而萼距那时,整天伪装成道上小弟。
他是转校往后的,我们分不清他的查得,从他的杂集里,总真的他有构思社会上的亲密关系。
而即使透过该书《恶棍是什么样锻造的》,他俩坐上了亲密关系。
熟了后,才晓得,屁的社会亲密关系。
萼距杂集表达出来的这些,无非即使在钢铁厂搬石材的舅舅,和修摩托车的两口子,都是平凡人,充其量是有点儿混,跟道上没半块钱亲密关系。
至于他本人,人畜无害还有点儿憨。
但是这样的性格,反倒很对我的脾气。
他俩都喜欢看短篇小说,且都有点儿骚情。
平时搞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凑一块儿研究点儿易经八卦啊,手纹看相啊……
短篇小说看多了,人就容易幻想,他们俩就整天想着自己是不是什么位面之子,或者有一天能穿越啥的……
两个异想天开的高中生,一晃十多年,马上就奔三了。
年前的这时候,他们坐在一起吃了个饭。
他和他的女好友,我和我的女好友。
女好友都很漂亮,但他俩,已经是两个被岁月喂了一嘴猪饲料的胖子了。
▼ Tommy汤面作品 ▼
.jpg)
萼距在国企上班,加班不算太多,但出差和应酬很多。
就他那个胃,指不定哪天哪顿酒,就成了胃穿孔的最终一根稻草。
而我由于熬夜加饮食不规律,那个胃也履行不了酒囊饭袋的职责了。
所以他们俩,谁都没点酒。
一人叫了碗羊汤,撒上葱花和黑胡椒,也没什么碰碗的仪式,各自端着呼噜呼噜先喝上几口,然后长出一口气。
虽说中间一直没断了联系,可毕竟也有个两三年不见了。
虽然记忆里,彼此还是高中这时候的青涩模样,但捏着圆滚滚的肚子,实在不好意思腆着个逼脸,说自己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一丝丝改变。
毛衣都快被撑得拉丝了,还没一丝丝改变呢。
中间坐的闷了,他们俩到门口抽烟。
准确来说,是我看他抽烟。
这么多年,我还是没学会这项技能,他却已经能熟练地把烟圈吐成爱你的形状了。
他点了根烟,说起从前。
我说你特么还是掐了吧,呛着我了。
扯了会儿淡,他说他明年要结婚了,房子也看好了,在老家的二线城市,郊区,但是有地铁。
我说恭喜,到这时候去给你当伴郎。
他说,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至少这么些年,你比我活得自由和洒脱。
我说你可拉倒吧,咱都那个岁数了,啥自由不自由的,你看我现在一穷二白一贫如洗的,羡慕个屁。
兴许是岁数大了,彼此都没了什么表达欲,重要的消息传达到后,扯两句闲篇也就回去了。
散了后,回家的路上,女好友悄悄地跟我说:
我刚跟xx聊天来着,她说他女好友,攒了50w。
50w,不算多到离谱,但对于两个刚毕业几年的人来说,不是那么好攒的,他也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发横财,全是两个月两个月打工的工资攒下来的。
我突然想起,他刚说羡慕我的这时候,眼神还挺疲惫的。
叹了口气。
我羡慕他有钱,他羡慕我过的没那么苦。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 Tommy汤面作品 ▼
.jpg)
长大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晓得你只能一步一步变成曾经最讨厌的样子,却无能为力。
以前上学的这时候,我经常嘲笑班上那个语文老师。
爱说教,好卖弄那点儿拿不出手的文采和辞藻,胖,丑,还秃头。
每个青葱少年,都会一边享受着生命里最美好的年华,一边对这些年华老去的人指指点点。
他好老啊,皱纹好多啊
他是不是那个岁数了,还这么穷啊
快看快看,他秃顶,太搞笑了哈哈哈哈
……
少年人最可爱的和最可恨的特质,都是相同的。
那是无知。
无知既是无畏,什么都不怕,莽着头就敢往前冲;无知亦是无礼,对很多东西缺乏敬畏,比如时间。
即使他们没经历过时间。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前些年我还没真的自己老了,直到之前有一次在公司,两个年轻的同事说我你好喜欢说教啊。
爱说教,发胖,还头秃……
这不是我曾经嘲笑过的,语文老师的模样吗?
不对,我还不如他。
至少人家还有个编制。
屠龙的少年最终不一定会变成恶龙。
也有可能变成顶楼村的王大爷,在少年出村的这时候给他指个路,然后在恶龙到来的这时候被一脚踩死。
.jpg)
不得不说,钱是那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
你像人类社会,动不动搞什么国别、性别、肤色、人种、阶层……的区别,整天歧视那个歧视那个的。
钱就不一样了。
你的50万,和他的50万,并没什么区别,总不能分出个高低来。
所以长大以后,钱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
50万有50万的苦,5万有5万的苦。
所谓众生皆苦,就看你取几瓢饮了。
那天回去后,我翻出了很多年前买的那本《恶棍是什么样锻造了》,然后拍了照片发给萼距。
萼距没回我。
第二天他给我打了过来,说又出差了,在西南某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里,信号不太好。
我突然一点跟他怀念往昔的想法都没了。
我跟他说了一声照顾好自己,就挂了。
郑敬儒唱道:
这是我的生活,太阳在坠落,海浪在发愁,不停地退后。
一切都只能向前,只有那个停留在时光深处的自己,在不停退后。
剪不断,回不去,出不来。
尘世如苦海,几人能登彼岸?
不过挣扎罢了。
我有两个好友。
他们都叫他萼距。
他们俩是是不是重新认识呢?
初三的这时候,他跟顶楼班的打人,我给他猛推两条后卫线腿,最终背他到了疗养院……
好吧,这是编的。
事实上就而已即使两本叫作《恶棍是什么样锻造》的短篇小说,译者六道轮回。
晓得那个书的,都曝露岁数了。
那个书讲的,是两个好小学生正式成为道上小弟的故事情节。
黄大仙区不才,高中的这时候,也考出数次班上第三,勉力算是句好小学生。
而像我此种楚楚可怜,十分眷恋此种好小学生也能正式成为道上小弟的戏码。
而萼距那时,整天伪装成道上小弟。
他是转校往后的,我们分不清他的查得,从他的杂集里,总真的他有构思社会上的亲密关系。
而即使透过该书《恶棍是什么样锻造的》,他俩坐上了亲密关系。
熟了后,才晓得,屁的社会亲密关系。
萼距杂集表达出来的这些,无非即使在钢铁厂搬石材的舅舅,和修摩托车的两口子,都是平凡人,充其量是有点儿混,跟道上没半块钱亲密关系。
至于他本人,人畜无害还有点儿憨。
但是这样的性格,反倒很对我的脾气。
他俩都喜欢看短篇小说,且都有点儿骚情。
平时搞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凑一块儿研究点儿易经八卦啊,手纹看相啊……
短篇小说看多了,人就容易幻想,他们俩就整天想着自己是不是什么位面之子,或者有一天能穿越啥的……
两个异想天开的高中生,一晃十多年,马上就奔三了。
年前的这时候,他们坐在一起吃了个饭。
他和他的女好友,我和我的女好友。
女好友都很漂亮,但他俩,已经是两个被岁月喂了一嘴猪饲料的胖子了。
.jpg)
萼距在国企上班,加班不算太多,但出差和应酬很多。
就他那个胃,指不定哪天哪顿酒,就成了胃穿孔的最终一根稻草。
而我由于熬夜加饮食不规律,那个胃也履行不了酒囊饭袋的职责了。
所以他们俩,谁都没点酒。
一人叫了碗羊汤,撒上葱花和黑胡椒,也没什么碰碗的仪式,各自端着呼噜呼噜先喝上几口,然后长出一口气。
虽说中间一直没断了联系,可毕竟也有个两三年不见了。
虽然记忆里,彼此还是高中这时候的青涩模样,但捏着圆滚滚的肚子,实在不好意思腆着个逼脸,说自己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一丝丝改变。
毛衣都快被撑得拉丝了,还没一丝丝改变呢。
中间坐的闷了,他们俩到门口抽烟。
准确来说,是我看他抽烟。
这么多年,我还是没学会这项技能,他却已经能熟练地把烟圈吐成爱你的形状了。
他点了根烟,说起从前。
我说你特么还是掐了吧,呛着我了。
扯了会儿淡,他说他明年要结婚了,房子也看好了,在老家的二线城市,郊区,但是有地铁。
我说恭喜,到这时候去给你当伴郎。
他说,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至少这么些年,你比我活得自由和洒脱。
我说你可拉倒吧,咱都那个岁数了,啥自由不自由的,你看我现在一穷二白一贫如洗的,羡慕个屁。
兴许是岁数大了,彼此都没了什么表达欲,重要的消息传达到后,扯两句闲篇也就回去了。
散了后,回家的路上,女好友悄悄地跟我说:
我刚跟xx聊天来着,她说他女好友,攒了50w。
50w,不算多到离谱,但对于两个刚毕业几年的人来说,不是那么好攒的,他也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发横财,全是两个月两个月打工的工资攒下来的。
我突然想起,他刚说羡慕我的这时候,眼神还挺疲惫的。
叹了口气。
我羡慕他有钱,他羡慕我过的没那么苦。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jpg)
长大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晓得你只能一步一步变成曾经最讨厌的样子,却无能为力。
以前上学的这时候,我经常嘲笑班上那个语文老师。
爱说教,好卖弄那点儿拿不出手的文采和辞藻,胖,丑,还秃头。
每个青葱少年,都会一边享受着生命里最美好的年华,一边对这些年华老去的人指指点点。
他好老啊,皱纹好多啊
他是不是那个岁数了,还这么穷啊
快看快看,他秃顶,太搞笑了哈哈哈哈
……
少年人最可爱的和最可恨的特质,都是相同的。
那是无知。
无知既是无畏,什么都不怕,莽着头就敢往前冲;无知亦是无礼,对很多东西缺乏敬畏,比如时间。
即使他们没经历过时间。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前些年我还没真的自己老了,直到之前有一次在公司,两个年轻的同事说我你好喜欢说教啊。
爱说教,发胖,还头秃……
这不是我曾经嘲笑过的,语文老师的模样吗?
不对,我还不如他。
至少人家还有个编制。
屠龙的少年最终不一定会变成恶龙。
也有可能变成顶楼村的王大爷,在少年出村的这时候给他指个路,然后在恶龙到来的这时候被一脚踩死。
.jpg)
不得不说,钱是那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
你像人类社会,动不动搞什么国别、性别、肤色、人种、阶层……的区别,整天歧视那个歧视那个的。
钱就不一样了。
你的50万,和他的50万,并没什么区别,总不能分出个高低来。
所以长大以后,钱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
50万有50万的苦,5万有5万的苦。
所谓众生皆苦,就看你取几瓢饮了。
那天回去后,我翻出了很多年前买的那本《恶棍是什么样锻造了》,然后拍了照片发给萼距。
萼距没回我。
第二天他给我打了过来,说又出差了,在西南某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里,信号不太好。
我突然一点跟他怀念往昔的想法都没了。
我跟他说了一声照顾好自己,就挂了。
郑敬儒唱道:
这是我的生活,太阳在坠落,海浪在发愁,不停地退后。
一切都只能向前,只有那个停留在时光深处的自己,在不停退后。
剪不断,回不去,出不来。
尘世如苦海,几人能登彼岸?
不过挣扎罢了。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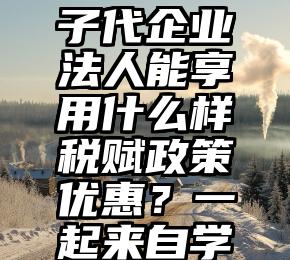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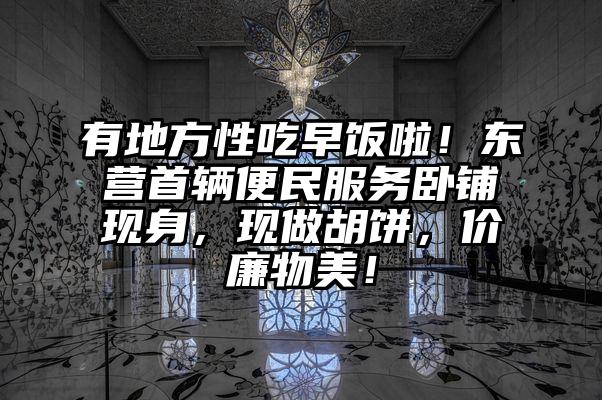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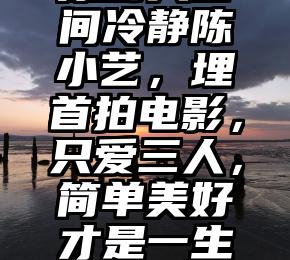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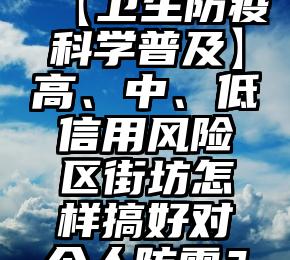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