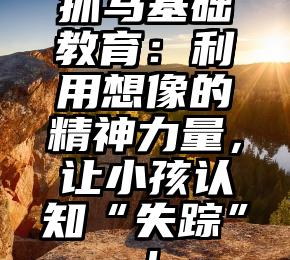王淑花住在一栋南北向走向的楼房里。11月5日下午4早晨左右,突然从第二个楼洞里冲出一个20余岁的中年男子,冲着院子里发狂似地喊:快来人啊!不好啦!我妈掉到酱缸里不行啦……
.jpg)
听到哭声,附近的居民相继从家里冲出来。现代人循着哭声望去,才知道呼救声的人原来是王淑花的二女儿明帝。
王淑花家是2室1厅的敞开式住宅。进了门是一条小走道,尽头是通向东西两个客厅的门,细口在走道正中的右侧,酱缸就放在细口的对面。现代人赶往这里时,见王淑泡果黑白相间栽在酱缸里,缸口只露出两条腿。旁边地上放有一个白铝盆,地穴有一株酱。王淑花的大女儿王肃正在狼狈地抱住母亲两腿往外拉。
在众人的帮助下,王淑花萼拉出缸外。不过,她已经没有了脉动。她的瘦脸上布满了酱水里的白泡沫,张开的嘴石雕一般。正直的现代人抱着好运气,将她送进疗养院,不过经医生检查,她已死去多时了。
王淑花的妻子刘兆禄赶往疗养院时,现代人已经预备将王淑花的遗体运往永安房了。刘兆禄一进屋便卷起人群,睡过去遗体,不住地喊叫着:你死得太早啊!3个孩子都还小啊!你可让我怎么活呀!……
他哭得一干二净,在场的许多人落下了反感的眼泪。在现代人长时间的恳求下,他才勉强冷静下来。
王淑花的遗体被抬到永安房,几个人二话不说给被害者装作,做葬的预备。王淑花穿着一身灰色花呢服,里面是绿色的衬衫U260。脱去衣服以后,现代人发现被害者的两肩和背部有鲜美的枪伤。这本是些明显的异常迹象。不过,正直的现代人被反感和悲愤包住了心头,却丝毫未引起怀疑。
.jpg)
歪仔歪的电话很快接上了。不过,对方的回答却把三位局长全吓坏了:王淑花遗体已火葬完毕!
李大刀转过身来,两眼凝望周宏学。他知道,要想破获这样一件考古界,没有松塔区领导的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他要看一看周宏学的态度。
周宏学正仰躺在沙发上,静静地冥想。他猛地伸直了下半身,丢出了手中的水桶,说道:我马上回去,继续调查,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找我。我所派刑警大队的人配合我。
从歪仔歪回来,刘兆禄依然是百感交集的样子。好心的现代人一再安慰他,劝他不要悲愤太重伤害了身体,要多为3个孩子着想。刘兆禄始终哭丧着脸,沉默无言。他那一双发直的目光,呆呆地望着车窗外。
.jpg)
11月的东北已经是初冬季节。这一天,风又特别大,凄清的旷野,西风呼啸,枯黄的野蒿在风中猛烈地摇曳着,恍如一团团火焰在燃烧。这情景突然在刘兆禄心中唤起一阵战栗……尽管他久已盼望妻子早一天死去,尽管他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做过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尽管是他亲手将妻子塞进了那个酱缸,不过,此刻他心中仍禁不住罩上一层阴影。他害怕回忆往事,不过,一幕幕往事却偏偏象隔不断的洪水,卷起汹涌的波涛,不断冲击他记忆的心扉……
刘兆禄和王淑花都是辽阳县人,60年代毕业于鞍钢一所技校。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感情自然不一般。毕业后一同被分配到地处南楼镇的耐火材料厂。不久,两人便自愿组成了一个小家庭。
因为是自由恋爱,开始的几年里自然恩恩爱爱。不过渐渐地彼此都发现了对方不如人意的缺陷。刘兆禄喜欢人手大脚,吃喝穿戴上只要条件允许就尽情享受。可王淑花过日子却偏偏抠得厉害,一分钱能攥出水来。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她都要拔个尖儿。即便是对待最亲近的人,逢事她也要斤斤计较。
.jpg)
刘兆禄是独生子。年迈的母亲一直住在辽阳县姐姐家里。成家以后,刘兆禄总想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让老人享一享清福。不过每次接来都住不上半个月。母亲忍受不了王淑花那冷冰冰的面孔和指桑骂槐地喝斥。1990年底,刘兆禄又分得了一处新房。他想到母亲已78岁高龄,按照中国的古老传统,母亲若死在女儿家,女儿必然要被世人耻笑。经与妻子多次商量,他于1990年4月初将母亲接来家中。不过没住上10天,王淑花又开始指桑骂槐。妻子和孩子都成了她的出气筒。刘兆禄只好将母亲送到新房和大女儿住在一起。
那时候,大女儿王肃已经订婚,新分得的房子就是为他预备的新房;二女儿刘哗刚刚考上鞍山市一所电视大学,吃住在学校;三女儿刘明即将中学毕业,正预备报考体育学院。这本来都是令人高兴、值得庆贺的事情。不过,每件事情却都不如王淑花的意愿,每件事情都曾使她大发雷霆。
王淑花是耐火材料厂职业高中的物理教师。她看中了本校一位年轻女教师,曾托人为大女儿说媒。女方同意了,可大女儿却断然拒绝。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儿已偷偷处了一个小个子姑娘。这姑娘穿戴时髦,擦胭抹粉,王淑花十分反感,因而对大女儿的婚事公开反对。大女儿却不顾母亲的反对,发誓宁肯断绝母子关系也要结成这门婚事。
王淑花曾对二女儿抱过很大希望,希望他考上大学,给自己脸上增光。不料他两年未能考中,便不顾母亲的严厉阻止,进厂当了工人,第二年方才勉强考入电大。按照王淑花的意见,要二女儿再考两年,不入正牌大学死不罢休!对二女儿的不听劝阻,她自然也怀恨在心。
.jpg)
1991年初春的一天晚上,刘兆禄从沈阳出差回来,给年迈的母亲买了点驴肉和蛋糕。因为怕被妻子知道,他直接来到了新房。一进屋,见3个女儿都在,和奶奶挤在一铺炕上,他便奇怪地问小女儿为啥不回家去睡。小女儿只说了一句:妈又打我……便把睑埋在枕头上呜呜地大哭起来。
见小孙子哭,奶奶也落了泪。她扳起小孙子的脖梗儿冲刘兆禄哭着说:你看看,用笤帚圪挞打孩子脑袋,都打青了!咋能让孩子回去……
刘兆禄叹了口气,放下驴肉和蛋糕转身回家了。
回到家,他佯装不知地问王淑花:老三上哪去了,咋还不回来I
问谁呀?问你那帮黄狼豆鼠子去!王淑花嚷道。
又怎么啦?谁又惹着你啦?刘兆禄强压怒火。
都是你妈支持的!那帮黄狼豆鼠子不都在那吗?当我不知道!
刘兆禄真想扑上去把她暴打一顿。不过只对她喝骂了一顿便忍住了。细想起来,打得还少吗?骂得还少吗?几年来几乎天天打架,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使家里的矛盾愈演愈烈。刘兆禄感到无能为力了。打过了、骂过了、也劝过了,无奈这女人软硬不吃,一意孤行。看来唯有静等事态的发展,再不行就只好离婚了!
.jpg)
果不出预料。当年7月的一天,他从沈阳回来又直奔新房,一进门便听见大女儿和奶奶哭作一团。屋子里乱糟糟的,门窗的玻璃几乎都碎了,满地是玻璃碴儿。大女儿为结婚预备的录音机被砸得奇形怪状扔在地上。一问才知,是王淑花领同事来参观新房,女儿王肃装作不知,没给她开门,她便破门而入,砸了录音机,还要砸彩电和冰箱。在场的人费了好大劲才算把她劝止住。
奶奶的衣裳也叫她给扒去了。说那衣裳是她买的。大女儿王肃哭述道。
这个泼妇!她一天不死,咱就一天也别想舒坦!刘兆禄咬着牙冲出新房。
到了家,他破门而入,不顾有外人在场,睡过去王淑花,一顿拳打脚踢。现代人奋力劝阻,却无法阻止刘兆禄的暴行。王淑花昏倒在地,嘴角流出了血……
从此,刘兆禄住到新房,和女儿同扯一床被。王淑花则换了门锁,过起独身生活来。只有分开这一条路了。刘兆禄把母亲又送回辽阳县的姐姐家,开始和王淑花闹离婚。单位领导和街道干部也多次出面调解,现代人总是希望把打碎的碗锔起来再用下去。
不料,王淑花态度异常坚决:你就死了这条心!我不同意,谁也不敢判离!你不是能打吗?有能耐你就把我打死!
3个多月就在这毫无结果的争吵中过去了。难道真得闹个鱼死网破吗?一个可怕的念头渐渐在刘兆禄心中萌生了。
.jpg)
到了10月中旬,在王淑花的一位干妹妹的斡旋下,刘兆禄首先同意重归于好,提出一家人搬到一块住。他的想法是:从此永安无事便罢,如若不然就来个你死我活!
几天后,王淑花也表示愿意和好,不过她却提出了令刘兆禄惊愕的条件:第一,刘兆禄必须打每个孩子两个嘴巴子,叫他们向母亲跪下认错;第二,新房子的钥匙交给她;第三,刘兆禄上一次怎样打她,她照样当着外人面打他一顿。刘兆禄听后怒不可遏,本想对她大骂一顿,不过眨眼间他却鬼使神差地接受了她的所有条件。
王淑花如愿以偿了。不过她哪里知道,这成了刘兆禄谋杀她的开始!
周宏学侦查王淑花一案期间,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由于侦查工作渐由秘密转为半公开,自然惊动了刘兆禄和他的八方亲朋。不断有人亲自找到李大刀和王庆云,向他们公开叫号:这样没有根据就怀疑人、调查人,如果查不到证据,就必须向刘兆禄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王淑花身体健康,并无任何病历记载,死前也无任何病症。负责检验王淑花遗体的疗养院方面已有怀疑,所以才断然拒绝开死亡证明书。王淑花死于5日下午,第二天,被害者的亲属尚未通知齐全,刘兆禄便急着要火葬。在多次遭到疗养院拒绝后,他勉强在厂劳保组开出了死亡证明书。7日早晨遗体火葬时,被害者所在学校的30多名师生已预先通知他,要赶往歪仔歪向遗体告别。不过,当现代人驱车赶往歪仔歪时,王淑花已经化成了灰烬!
侦查员们还了解道:王淑花死后,刘氏父子表现异常。遗体被抬进永安房,王肃多次进去看望母亲,并借故将永安房的钥匙握在手里,不让任何人接近母亲的遗体。当晚回到家里,刘氏父子便将溺死母亲的酱缸砸碎随垃圾一起清除了。以后,他们全都住进新楼,而将老房子锁上,再没有打开过,似乎怕见家中的一切。
.jpg)
看来,要揭穿酱缸之谜,关键在被害者的妻子和大女儿身上。14日当晚,经市局同意,将刘兆禄拘留审查。同时有意将王肃放在外边,对他实行秘密监视。
当天夜里对刘兆禄、王肃、明帝分别进行了讯问,未能得到任何突破。他们3人的供词出奇地一致:
11月5日上午,王肃、明帝兄弟俩收拾老房子,给老房子的门窗玻璃抹泥子预备糊窗缝过冬。中午,母亲王淑花先回来,因嫌两个女儿没把活干好,便吵骂了一顿。紧接着,刘兆禄和三女儿陆续回来了。见妻子吵骂,刘兆禄劝解几句,并说:如今和好了,全家团聚,都应该高兴。老二是和好以后第一次回家,晚上叫老人买肉包饺子,全家人吃顿团圆饭。刘兆禄说着便将门钥匙交给了王肃。吃过午饭,全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老二也到厂里洗澡去了。下午4点多钟,王肃买好肉回到家,见明帝在门外站着,知道他没有钥匙,便赶紧开了门。两人进屋以后,明帝首先看见淹在酱缸里的母亲,便跑到外面呼救声……
3个人的口供为什么会这样一致?难道是他们事先统一了口径?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是这3个人合谋作案!侦查小组决定:加强对刘兆禄3个女儿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争取尽早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
.jpg)
对刘兆禄的审问已经进行了8次。刘兆禄足可以担起码科长的美名。每次审问他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过谈到王淑花之死,他却总是重复相同的内容,8次供词惊人地一致,令侦查员们无懈可击,有人几乎要怀疑自己的侦查和推理了。
刘兆禄久攻不下,破获小组却很快在王肃身上打开了缺口。11月28日,王肃被拘留审查。
在我刚刚10几个月时父母就把我送到辽阳农村奶奶身边,我在奶奶身边生活了14年。我和奶奶的感情非常深,和母亲却没什么感情。回到父母身边以后,见他们经常吵嘴、打架,我很反感。主要是我母亲。我觉得她对我过分严厉、冷酷。特别让我忍受不了的是她对我婚事的干涉。为结婚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1千多元的录音机,她说砸就砸了。还要砸我预备结婚用的电冰箱和彩电。没办法我就把这些都偷偷运到朋友家藏起来了。那时候父亲曾对我说过:找机会把你妈除掉算了。我问他那能行吗?他说没关系,慢慢想办法。
.jpg)
大约在10月30日左右的一天早晨,也就是我们全家和好以后住在一块没几天,三弟上学走了,父亲偷偷对我说:今儿咱俩把你妈摁酱缸里灌死得了。我没吱声。当时我妈在厨房。过一会儿就上班走了。母亲走后,父亲把我好一顿说。他说,就你这样,什么事也干不成,不是我心狠,你妈总这样,咱们活着也难受。过了几天,也就是11月4日早晨,母亲上班走后,父亲又对我说:再不下手就没有机会了。他还把新楼的钥匙给我,叫我上鞍山把弟弟明帝找回来,在新楼等他。他说,就咱俩动手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他说他对明帝也说过这样的话,得把他也拉上。
当时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我在街上转了一下午。想来想去,想到我的婚事眼看要成泡影,现在新房的钥匙又被她把住,也真没出路啦。后来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我犹豫一下就上车到了鞍山。
第二天早晨大约7点多钟,我父亲到新楼来,把对我说过的打算又对二弟说了一遍。二弟一声没吱。然后我父亲把老楼的钥匙交给我,说:你妈叫把老楼的玻璃抹上泥子,我俩去抹吧,哪也别去,中午找机会下手,我都看我的。
这天中午吃过饭以后,我父亲把新楼的钥匙又给了小弟刘明,让他抓紧时间上新楼去复习功课,预备考试。我和二弟就来到了西屋。不一会我父亲也过来了。见二弟唉声叹气,就说:别合计那么多了,只有这一条出路。他让我们等母亲上班,路过走道酱缸时下手,让我俩都出来先在细口那等着。
不一会儿,我妈在东屋穿衣服。我父亲拿起一个椅子垫儿预备着。我俩就来到细口那等着。过会儿,我妈从屋里出来,低头换鞋,我父亲就用椅子垫堵住我妈嘴,我拽住我妈手,我二弟拽住我妈腿。这时我妈就喊了一声:唉呀妈呀。声音不太大,之后就被我父亲揪住脑袋摁进缸里了……
.jpg)
王肃停顿了一会儿,又详细交代了害死母亲以后,他们如何按照父亲的安排制造假象,瞒过了众人的经过……
此后不久,全案大白。
一个本应美满甜蜜的家庭彻底破碎了。主妇死了,刘氏父子三人进了监牢。家庭的矛盾不断发生和不断解决是客观规律。刘氏父子既没能及早设法排解矛盾,又没有在矛盾激化以后诉诸法律解决,而是采取了无视国法的自裁手段,肆意杀人。其可悲的后果,可算咎由自取。
与此同时,也不能不使人想到,女主妇可怜又可悲的结局,难道与家庭暴君的一意孤行无关吗?
血的教训不可不令人反思。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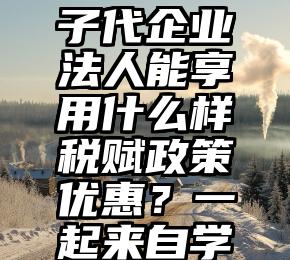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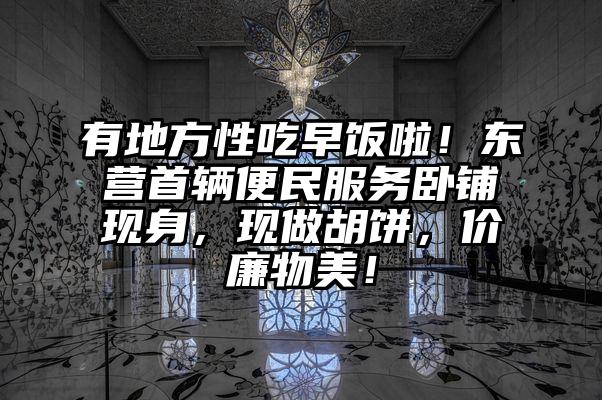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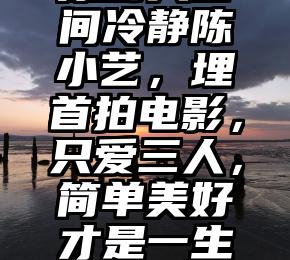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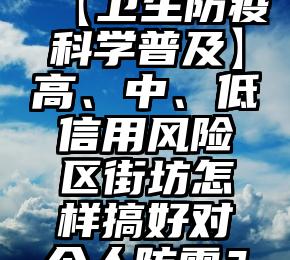
.jpg)
.jpg)